|
|
马上注册登陆,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用户注册

x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消息 创办《人间》杂志的台湾知名作家陈映真于11月22日在北京病逝,享寿79岁。
陈映真的夫人陈丽娜稍早将噩耗通知在台湾的弟弟陈映和后,陈映真死讯才在台湾近亲友人间传开。陈映真本名陈永善,1937年11月8日于新竹出生,2016年11月22日病逝北京,享寿79岁。陈映真于2006年6月移居北京后,自当年9月起接连中风,卧病至今已长达10年。
台湾作家陈映真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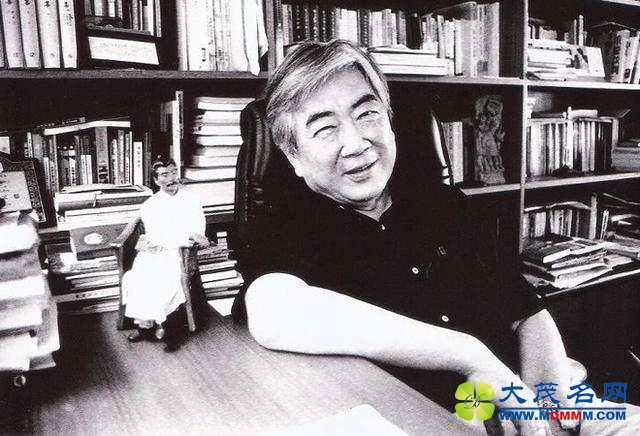
陈映真
陈映真是台湾文学重要旗手,代表作有小说《我的弟弟康雄》《上班族的一日》《苹果树》《铃珰花》《忠孝公园》等,评论《知识人的偏执》《孤儿的历史、历史的孤儿》《西川满与台湾文学》《中国结》等,以及散文若干。他的作品受鲁迅影响颇深,主要以描写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心态为主,色调忧郁苦闷,充满人道主义关怀;后期作品焦点转变为跨国企业对第三世界经济、文化与心灵的侵略。
陈映真原名陈永善,台北莺歌人,1937年10月6日出生。他本名陈永善,后用过笔名许南村、赵定一、陈善、石家驹等。笔名“陈映真”原是其早逝的孪生兄长的名字。1957年成功高中毕业后考取淡江文理学院(即今淡江大学)外文系。1959年,还是大学学生的陈映真便以第一篇小说《面摊》出道文坛。
1968年7月,台湾政府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逮捕包括陈映真、李作成、吴耀忠、丘延亮等36人,此案被称为“民主台湾联盟案”。陈映真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陈映真曾说过,在此经历之后,“对自己走过道路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由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走向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的知识分子”。
1975年,陈映真因蒋介石去世百日特赦而提早三年出狱,出狱后仍然从事写作,转趋现实主义,并且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发表多篇重要文章,成为乡土文学论战的重要旗手。
上世纪80年代,陈映真继续参与《文季》《夏潮》等杂志的编务,并且在“中国结”与“台湾结”论战中与台湾本土派人士交锋。1985年11月,陈映真创办以关怀被遗忘的弱势者为主题的报道文学刊物《人间》杂志(至1989年停刊)。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陈映真于2006年6月移居北京,9月起就接连中风,因而卧病至今已长达10年。由于陈映真年事已高且健康未见好转,部分好友与支持者曾私下推动陈映真能返回台湾,至少可以“落叶归根”。但考虑到陈映真身体欠佳,陈映真夫人陈丽娜一直未同意丈夫回台湾。
相关阅读:
钱理群:陈映真和“鲁迅左翼”传统
台湾作家陈映真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陈映真
一、鲁迅对陈映真的意义
陈映真自己有两个说明:“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1],“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2],两句话都很值得琢磨。
据陈映真的自述,他是在“快升(小学)六年级的那一年”(那就应该是1949-1950年间),偶然得到了一本鲁迅的《呐喊》。
陈映真回忆说:
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我于是才知道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地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一个中国的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3]
陈映真如此去解读鲁迅的作品——把鲁迅看作是现代中国的一个象征,特别是现代中国的左翼传统的载体,所感受到的,所认同的是鲁迅背后的“中国”,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其中有特殊的台湾问题在。如陈映真一再强调的,1950年在当代台湾思想文化文学史上是一个转捩点:在此之前,特别是在1945-1950年间,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作品被大量介绍到台湾,“日政下被抑压的台湾文学激进的、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传统,在这五年间迅速地复活,并且热烈的发展”;但从1950年开始,随着世界冷战结构的确立,“左翼的、激进的,经中国30年至40年发展下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思潮,在这个时代里,受到全面压制”,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遭到全面封杀,从此,台湾的思想、文化、文学与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特别是其中的左翼传统发生了断裂。[4]未来台湾最重要的作家陈映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和鲁迅相遇,这实在是历史性的。它象征着、预示着在地表的断裂下的地层深处的相承相续。而陈映真本人正是在这样的相承相续里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因此确立了他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其实,未来的陈映真也就是在这相遇中确立了。首先,是一种我们可以称为“陈映真的视野”的确立。如日本研究者松永正义所说:“这样的鲁迅体验所给予陈映真的,是使他能够尽管他目前身处在‘台湾民族主义'的气氛中,他还能具备从全中国的范围中来看台湾的视野,和对于60年代台湾文坛为主流的‘现代主义',采取批判的观点”。[5]我要补充的是,陈映真还通过鲁迅,获得了从第三世界看台湾的视野;记得鲁迅说过,他是从俄国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6],在我看来,陈映真也是从鲁迅的文学里,明白了这样一件大事,从而在这全球化的时代,确立了自己的第三世界立场,并且把台湾文学置于第三世界文学的大视野里。陈映真一直铭刻在心的是他父亲给他定下的三重自我定位:“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最后,你才是我的孩子”[7]。我们也可以说,陈映真也是赋予台湾与文学以三重定位:“第三世界的台湾与文学,中国的台湾与文学,台湾的台湾与文学”。这样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视野和立场,在台湾的思想、文化、文学界可能是相当独特的。
这也就决定了陈映真的命运。他这样写道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之间的深刻分歧和他的情感反应:
几十年来,每当我遇见丧失了对自己民族认同的机能的中国人;遇见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抱着无知的轻蔑感和羞耻感的中国人;甚至遇见幻想着宁为他国的臣民,以求“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国人,在痛苦和怜悯之余,有深切的感谢——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集,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8]
我在这自述里,读出了陈映真的孤独和陈映真的坚定,这都深扎在他与鲁迅的精神相遇相通里。
对于陈映真所说的“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我们还需要作更具体、深入的讨论。
于是注意到陈映真的“人民为主体的爱国论”[9]:“在中国的民众、历史和文化之中,找寻民族主体的认同”,“找思想的出路,找心灵的故乡”[10]。他反复强调一点:“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最高诰命,来自人民——而不是那一个党,那一个政权”[11],“一个独立的批评的作家,应该认同于自己的人民、文化与历史,而不是认同那一个个别的政党与政权”[12],“中国的作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受到批评和抑压的时刻开始,彰显了他们的一体性:他们属于中国的人民,而不属于任何权力”[13]。
这是一个“在权力之外,另求出路”的思路,是一个自觉地“重建中国知识分子在权力之前,坚持良知、真理,为民请命,褒贬时政的传统精神”的努力[14]。这也是“当永远的在野派”,做“抵抗体制的知识分子”的选择和自我定位。[15]陈映真作出这样的选择与定位,鲁迅无疑是他的重要精神资源和榜样。鲁迅一直在告诫我们:要论中国和中国人,要“自己去看地底下”,那里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才是中国的“筋骨和脊梁”。[16]
而鲁迅更是把“对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永远的批判者的知识分子称为“真的知识阶级”。[17]这样的独立于党派外、体制外的批判知识分子的传统,是鲁迅所开创的;而陈映真正是这样的批判知识分子传统在台湾的最重要的传人和代表,陈映真也因此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史上获得了自己的特殊地位。
二、陈映真与“鲁迅左翼“传统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鲁迅所开创的“党派外、体制外的批判知识分子”的传统,及其与陈映真的关系,把讨论深入一步,我想提出与强调一个“鲁迅左翼”的概念。
最早提出问题的,是大陆鲁迅研究者王得后先生,他在《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2期上发表了《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异同论》一文,指出30年代的鲁迅文学和左翼文学既有许多重要的共同点,又存在着重大差异和原则分歧。在王得后先生文章的启示下,我想到30年代的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左翼传统,一个是“鲁迅左翼”,另一个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可以称为“党的左翼”。这两个左翼在30年代显然存在着基本的一致和深刻联系,以至很容易看作是一个群体:他们都反抗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以至形成了一个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左翼阵营,鲁迅曾经作过这样的概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18]鲁迅对这样的大左翼传统是认同的,并将同样从事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左翼文学家视为“战友”;但他也从不掩饰自己和这些战友的原则分歧,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最后“两个口号”的论争,就从未停止过。
正如王得后先生所说,“鲁迅步入左翼文学阵营前后的种种内部矛盾和争斗,根源在鲁迅思想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异同以及鲁迅文学和中国左翼文学的异同”,对此王文做了详尽的论析。我只想强调一点,党的左翼有一个高于一切的原则,就是所谓“党性原则”,也就是把党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而党的最高利益则是:在野时夺取权力和掌权以后的权力独占,因此,要求所有的党员、信奉者及其统治下的人民都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意志,而绝不允许发出和党不一致的声音。在“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主要罪状就是他在党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之外,另提一个“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正是“党的左翼”的大忌。同时也证明了“鲁迅左翼”的独立于“党的左翼”之外的意义。因此,鲁迅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和这些“政治革命家”的合作是有限度的,并且思考了自己这样的“永远不满足现状”的永远的批判者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他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里,尖锐地指出:“革命政治家“和“文艺家“开始反对旧的专制体制时,因为同是不满意现状,可以有某种程度的合作;但“革命成功“以后,革命政治家掌握了权力,就“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19]这是很能说明“党的左翼“和“鲁迅左翼”的区别、关系和“鲁迅左翼”的命运的。因此,在30年代中期,当鲁迅发现“党的左翼”中的某些掌权者已经演变成“革命工头”、“奴隶总管”时,就毅然与之决裂,并且作出革命胜利以后“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的预言。[20]
陈映真未必熟悉这段历史,但他对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中的“左”的倾向,是关注并有警觉的。他谈到“左翼文学的'党文学'”的问题:“简单化地,庸俗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理解为阶级斗争的武器,理解为为了革命、为了政治服务的单纯的工具,把创作自由的理念,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视为同一物。服从党、革命和无产阶级政治需要而创作,成为当时‘前进的革命文艺家'最高的诰命。谁要主张文艺创作的个人性、文艺创作的自由,谁就是堕落的资产阶级”。[21]他还专门谈到知识分子落入“偏致”和“党派性”的危害,特别是“为了有意无意地保卫一个既有的秩序——一个既有的所有权秩序、社会秩序,等等——而膨胀起来的时候,它就必然堕落为各式各样的教条,有时更纠集他们所掌握的一切强制力量——如舆论,如警察,如政府,如法律和军队,如法庭和监狱——来加强他们的阵容”,那是甚至会造成“罪恶”的。[22]这其实都是抓住了“党的左翼”的一些要害问题,[23]同时也是当年鲁迅所批判过的。陈映真所要继承、坚持和发扬的左翼传统,实际就是“鲁迅左翼”的传统,这大概是没有问题的。[24]
那么,陈映真所继承、坚持、发扬的“鲁迅左翼”传统,又包含什么内容,有什么特点呢?这是一个大问题,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与讨论。这里只能说说我所理解的几个要点,算是出几个题目吧。
首先自然是前文反复讨论过的“党派外,体制外的独立性”,和“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的批判立场”。这里要追问的是,这样的独立的、全面而彻底的批判立场的立足点,其背后的价值观念及终极性的理想与追求。
陈映真的回答是明确的:“文学与艺术,比什么都要以人作为中心和焦点”。[25]“放眼世界伟大的文学中,最基本的精神,是使人从物质的、身体的、心灵的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的精神。不论那奴役的力量是罪、是欲望、是黑暗、沉沦的心灵、是社会、经济、政治的力量,还是帝国主义这个组织性的暴力,对于使人奴隶化的诸力量的抵抗,才是伟大的文学之所以吸引了几千年来千万人心的光明的火炬。因为抵抗不但使奴隶成为人,也使奴役别人而沦为野兽的成为人”。[26]
以人为中心,追求人的自由,解放,健全发展,“使奴隶成为人”,为此,必须抵抗一切“奴役的力量”:陈映真的这一基本信念、理想、追求和价值观,是和鲁迅的追求“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立人“思想完全一致的。这可以说是鲁迅与陈映真所共有的“乌托邦”彼岸理想。我们说陈映真与鲁迅之间存在着精神的相通,这正是他们心灵契合之处:他们都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人的“物质的、身体的、心灵的奴隶状态”(后来陈映真用马克思的理论,将它称为“人的异化”[27]有着也许是过分的敏感,这其实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作家最重要最基本的精神素质。在他们看来,导致这样的人的奴隶状态的奴役关系,是广泛地存在于现代社会,来源于各个方面,并且会不断再生产,是永远存在于此岸世界的。而作为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用彼岸乌托邦的终极性的“立人”理想照亮此岸的黑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以各种形态,特别是以最新形态出现的奴役力量,进行无情的揭露与批判,不断向社会发出警示。这样的批判,就必然是全面而彻底的,而且是永无休止的,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永远不满足现状”,要作“永远的革命者”的真实而丰富的含义,也是鲁迅要提倡“韧性战斗”的最基本的原因。这大概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陈映真独特的“异端乌托邦”主义吧。[28]
这其实也是他们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对时代所提出的问题,所作出的回应。因此,鲁迅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东方专制主义(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传统文明中的“吃人
肉的筵宴”),但在30年代的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鲁迅又发现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以及西方现代文明病对中国的渗透与蔓延:在这些方面,他都看到了“吃人肉的筵宴”的再生产;而如前所说,鲁迅在他的晚年又在反抗运动内部发现了新的奴役关系,所谓“革命工头”的产生。因此,在他的遗嘱里,鲁迅宣布“一个都不宽恕”,正是表明,他是要把自己的彻底的批判立场坚持到底的,并以此期待后来者。
陈映真正是这样的坚持鲁迅式的彻底批判立场的后来者之一。但所面对的问题,却是鲁迅未曾经历的。于是就有了陈映真的从台湾问题出发的对殖民社会、“冷战/民族分裂“构造以及大众消费时代下的人的异化(各种形式的奴隶状态)的批判。但我以为,对陈映真最具有挑战性的,可能是他如何面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所发生的异化的问题:“以‘人间解放'为起点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如何逐步走上它自己的对立面,即‘人间残害'的另一端”。[29]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社会主义的中国曾经是他的理想所在,是他批判台湾社会的重要资源。这可以说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包括陈映真在内的所有的左翼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一个困境。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作专门的详尽讨论。这里只想概括地指出一点,陈映真很快就走出了这样的困境,依然坚守了他的彻底的全面的批判立场。第一,他并不回避中国社会主义实验中所出现的严重异化,并从新的奴役关系的产生的角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坚持“对于(海峡两岸)两个政权和党派,我们保有独立的、批评的态度”。[30]其二,他并没有像某些左翼知识分子那样,因为对社会主义的失望而走向全面认同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另一个极端,他旗帜鲜明地表示:对社会主义的“反省“绝不能”后退、右旋到了否定反帝民族主义、否定‘世界体系'四百年来对落后国的支配和榨取这个历史的、经验上的事实,到了肯定帝国主义压迫有理论,主张穷人必须接受富国支配才能发展论,和跨国企业无罪论的地步”。[31]因此,他在批判所谓“社会主义病”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对“先进国症候”的批判。[32]他并且提醒说:“没有对帝国主义采取断然的批判态度——甚至受帝国主义豢养的——'后进国家'民主、自由甚至人权运动,总是向着它的对立的方向——独裁的、镇压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33]:这里所表现出的独立批判知识分子的清醒,是十分难得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陈映真在如此复杂,甚至混乱的局势下,依然坚持他的乌托邦理想,他的社会主义信念,并且提出了“在现存共产主义体制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外,寻求一条自己的道路”的新的设想,他认为是“第三世界革新的知识分子”所应该承担的历史任务。[34]尽管这还是一个有待展开的命题,但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以上所讨论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全面、彻底、永远的批判、创造精神,在我看来,就是“鲁迅左翼”的核心精神。“鲁迅左翼”的另外三个特点,限于篇幅,就只能略说几句了。
其二,“永远要以弱者,小者的立场去凝视人、生活和劳动”,陈映真在一篇介绍日籍国际报道摄影家的文章里,概括了这样一条左翼知识分子的原则。[35]这和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里谈到“真的知识阶级”除了永远不满足现状外,还必须坚持“平民”立场,“感受平民的痛苦”,“为平民说话”,[36]其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鲁迅在“五四“时期提倡“幼者本位,弱者本位”,30年代又坚持和“革命的劳苦大众““受一样压迫”,“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的左翼方向,他终其一生,都在“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37]而在许多台湾知识分子的眼里,陈映真最重要的精神品质,就是他“同情一切被损害、被侮辱、被压迫的人们”[38],这样的相近相通都不是偶然的。
其三,鲁迅在上一世纪初,就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反抗和实践的知识分子。[39]在“五四”运动以后,他又有了这样的反省:“比较新的思想运动起来时,如与社会无关,作为空谈,那是不要紧的,这也就是专制时代所以能容知识阶级存在的原故”,“只是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时,那就危险了。往往反为旧势力所扑灭”。[40]这就是说,从从事思想启蒙到参与社会实际运动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最后十年的左翼鲁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反抗运动的结合,也正是顺应这样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一个自觉的选择。陈映真也有类似的精神发展趋向和生命体验,他说自己的“思想发酵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一种实践和运动的饥饿感,就是觉得老这样读书,什么都不做,很可耻”[41],因此,他很早就介入了实际反抗运动,并因此两度遭遇牢狱之灾。人们说陈映真不仅用小说、论文表达自己的思想,还是一个“使用‘肢体语言'的作家”,[42]这确实是陈映真区别于许多知识分子的特点,但也确实提供了知识分子的一种范式。
其四,也是我最为看重的,就是“鲁迅左翼”的自我批判精神。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43]陈映真也说过:“写小说,对于我,是一种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因此,评论者说他是最具“反省力与批判力”的
作家。[44]他的写作,既是为了批判社会,更是为了清理自己,在这方面,陈映真也是和鲁迅相通的。这一点,也将鲁迅和陈映真与许多所谓左翼作家区别开来。鲁迅在和创造社论战时,就说他最看不惯的就是他们的“创造脸”,也可以说是“革命脸”吧:一言一行无不是“创造”,无不在“革命”,实际就是要垄断创造,垄断革命。陈映真也说:“激进的文学一派,很容易走向'唯我独尊'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45]“唯我独尊”的背后,是自以为真理在手,自己的使命就是向芸芸众生宣示真理,进而垄断真理;而鲁迅这样的真的知识分子,却永远是真理的探索者,他和读者一起探索真理,也不断修正错误。因此,批判知识分子的批判的彻底之处,就在于他同时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自己。我甚至认为,鉴别是不是真的批判知识分子,就看他是否批判自己。
不难看出,“鲁迅左翼”是一份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它是我们所说的“20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要强调的是,这样的“鲁迅左翼”不仅属于鲁迅,它是所有的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左翼知识分子共同创造的,陈映真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也作出了自己的独立和独特的贡献。
三、未完成的话题
文章应该结束了,但似乎意犹未尽。我们从主要的方面,对“鲁迅左翼”及其陈映真的关系作了一个勾勒;这样的勾勒是明晰和必要的,但却有可能把问题简单化,遮蔽了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我赞同李欧梵先生的观察与分析,陈映真是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他既写实又浪漫,既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又有浓郁的颓废情操,既乡土又现代,既能展望将来又往往沉湎于过去,对人生既有希望又感绝望,对于社会既愿承担但也在承担的过程中感到某种心灵上的无奈……”[46]鲁迅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陈映真所受到的鲁迅的影响,他和鲁迅的精神共鸣,是远比我们这里的描述更为复杂和微妙的。
而且我们已经讨论的问题,也还未充分展开。例如同样是同情被压迫者,同样是参加社会实践“鲁迅左翼”和“党的左翼”的相同和差异、分歧,就有待作更具体更细致的分析。何况还有许多未及论述的方面。例如,陈映真在《父亲》、《汹涌的孤独——敬悼姚一苇先生》等文章里,提到他对鲁迅和30年代左翼的了解和认识,父亲和姚一苇、胡秋原先生都是重要的中间环节,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再如,许多研究者都提到陈映真创作中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关系,而鲁迅正是“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的文学倡导者,[47]他自己的创作也有这样的特点,或许这也是讨论陈映真与鲁迅小说创作的
关系的一个视角。而前文的一个注释里已经提到的陈映真自称自己是“从文学出发的左倾”,是“比较柔软,比较丰润”的左派,也颇耐人寻味,是可以进一步展开的。
陈映真与鲁迅,这是一个未完成的话题,我们的讨论仅是一个开始。
2009年8月26日-9月1日
注释:
[1]陈映真在香港浸会大学“鲁迅节座谈会”上的讲话,据香港《大公报》2004年2月23日报道。
[2]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作品集(六)·思想的贫困》,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3]《鞭子和提灯》,《陈映真散文集(一)·父亲》,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1-12页。
[4]《四十年来台湾文艺思潮的演变》,《陈映真作品集(八)·鸢山》,第211、213页。
[5]松永正义:《透析未来中国文学的一个可能性——台湾文学的现在:以陈映真为例》,《陈映真作品集(十四)·爱情的故事》,第233页。
[6]鲁迅:《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3页。
[7]《父亲》,《陈映真散文集(一)·父亲》,第146页。
[8]《鞭子和提灯》,同上,第12页。
[9]《答友人问》,《陈映真作品集(八)·鸢山》,第37页。
[10]《无尽的哀思——怀念徐复观先生》,同上,第65、66页。
[11]《答友人问》,同上,第36页。
[12]《陈映真来函》,《陈映真作品集(六)·思想的贫困》,第10页。
[13]《关于中国文艺自由问题的几个随想》,《陈映真作品集(八)·鸢山》,第60页。
[14]《无尽的哀思——怀念徐复观先生》,同上,第65页。
[15]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作品集(六)·思想的贫困》,第50页。《严守抗议者的伦理操守》《陈映真作品集(十二)·西川满与台湾文学》,第37页。
[16]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第122页。
[17]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卷,第226-227页。
[18]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全集》第4卷,第290页。
[19]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20页。
[20]李霁野:《忆鲁迅先生》,写于1936年11月11日,收《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1辑第68页,1979年上海书店据1937年初版本影印。
[21]《中国文学的一条广大出路——纪念〈中国人立场之复归〉发表两周年,兼以寿胡秋原先生》,《陈映真作品集(十一)·中国结》,第98页;《关于中共文艺自由化的随想》〈陈映真作品集(八)·鸢山〉,第159页。
[22]《知识人的偏执》,《陈映真作品集(八)·鸢山》,第16、17页。
[23]陈映真对30年代左翼的观察与认识,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胡秋原的影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还有待专门的研究与讨论。
[24]陈映真在《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载《上海文学》2004年1月号)一文里有一段自白很有助于我们理解陈映真的选择:“从文学出发的左倾,从艺术出发的左倾,恐怕会是比较柔软,而且比较丰润,不会动不动就会指着别人说,是工贼、叛徒,是资产阶级走狗,说鲁迅的阿Q破坏了中国农民的形象,像那种极'左'的。我想我比较不会走向枯燥的、火柴一划就烧起来的那种左派。”鲁迅大概也是属于“比较柔软,而且比较丰润”的左派吧。
[25]《云》序,转引自李瀛:《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陈映真作品集(六)·思想的贫困》,第12页。
[26]《思想的荒芜——读〈苦闷的台湾文学〉敬质于张良泽先生》,《陈映真作品集(十一)·中国结》,第112页。
[27]《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的诸问题》,《陈映真作品集(八)·鸢山》,第124页。
[28]《陈映真作品集编辑体例》,《陈映真作品集(六)·思想的贫困》,第5页。
[29]《思想的索忍尼辛与文学的索忍尼辛——听索忍尼辛在台北演讲的一些随想》,《陈映真作品集(八)·鸢山》,第69页。
[30]《严守抗议者的伦理操守——从海内外若干非国民党刊物联手对〈夏潮〉进行政治诬陷说起》《陈映真作品集(十二)·西川满与台湾文学》,第38页。
[31]《“鬼影子知识分子”和“转向征候群”——评渔父的发展论》,《陈映真作品集(十二)·西川满与台湾文学》,第119页。
[32]《你所爱的美国生病了……》,《陈映真作品集(八)·鸢山》,第229页。
[33]《台湾长老教会的歧路》,《陈映真作品集(十一)·中国结》,第69页。
[34]《思想的索忍尼辛与文学的索忍尼辛——听索忍尼辛在台北演讲的一些随想》,《陈映真作品集(八)·鸢山》,第71页。
[35]《相机是令人悲伤的工具——日籍国际报导摄影家三留理男剪影》,《陈映真作品集(七)·石破天惊》,第107页。
[36]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卷,第224页。
[37]这是鲁迅对德国左翼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评语,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鲁迅的夫子自道。见《〈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鲁迅全集》第6卷,第487-488页。
[38]王晓波:《重建台湾人灵魂的工程师——论陈映真中国立场的历史背景》《陈映真作品集(十一)中国结》,第20页。
[39]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8页。
[40]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卷,第227页。
[41]《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载《上海文学》2004年1月号。
[42]王晓波:《重建台湾人灵魂的工程师——论陈映真中国立场的历史背景》《陈映真作品集(十一)·中国结》,第19页。
[43]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300页。
[44]李瀛:《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访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六)·思想的贫困》,第17-18页,第12页。
[45]《模仿的革命和心灵的革命——访问菲律宾作家阿奎拉》,《陈映真作品集(七)·石破天惊》,第98页。
[46]李欧梵:《小序〈论陈映真卷〉》,《陈映真作品集(十四)·爱情的故事》,第19页。
[47]鲁迅:《〈黯澹的烟蔼里〉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01页。
台湾作家陈映真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
|
 |客服:0668-2886677QQ:75281068|大茂微博|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大茂名网
( 粤ICP备18149867号 )茂名市大茂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客服:0668-2886677QQ:75281068|大茂微博|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大茂名网
( 粤ICP备18149867号 )茂名市大茂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