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登陆,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用户注册

x

奥兹:巴以两国如果做不了情人,就做邻居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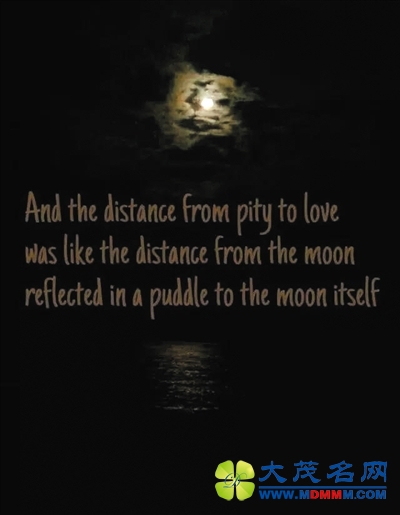
“怜悯之于爱,就像映照在水坑里的月亮之于月亮本身。”——奥兹
奥兹:巴以两国如果做不了情人,就做邻居吧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奥兹一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主张巴以双方通过妥协实现和解。1978年,他发起“现在就和平”组织。1992年,因对和平运动的卓越贡献,奥兹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奥兹说,任何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家园,哪怕这个家园小得不能再小。
奥兹,被誉为“以色列的良心”。人们说,“理解奥兹,千万不能忽略他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一面。”他说自己握有两支笔,一支笔写故事,另一支笔写政论,针砭时弊。
生长在旧式犹太人家庭、又蒙受犹太复国主义新人教育的奥兹,曾经也是“一只时刻准备为理想而献身的地下室里的黑豹”,他参加过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但现在,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是以色列“现在就和平”(Peace Now)组织的发起者,一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主张巴以互相妥协,比邻而居。
然而,在战乱和恐怖袭击不断出现在以色列人民生活中的今天,和平的步伐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迟缓。擅长破解家庭之谜的奥兹,依然会把巴以冲突理解成大家庭的内部矛盾。他说,如果真的无法相爱,就做邻居吧。
生活有巨大的惯性
新京报:距离你上一次来中国已过去了九年,这些年你在以色列过得怎样?
奥兹:我的生活一直很规律。现在我已经不住在沙漠小镇阿拉德了,全家都搬到了特拉维夫。我每天很早起床,日出之前,独自散步。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偶尔会对遇见的报纸投递员说声早上好。街道寂静,白色鸟群漫步街道,甚至能听见星星的低吟。散步回来后,我给自己泡一杯咖啡,坐在窗口张望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想着:如果我是这个人,会过什么生活?如果是那个人呢?如果我必须变成这个胖女人,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如果我要变成那个瘦子经理人呢?就这样迎来了日出,在书桌旁开始一天的工作。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即使火山喷发,以色列人依然在侍弄花草”,战乱和动荡似乎成了以色列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的一部分,现在依然是这样的生活状况吗?
奥兹:亲爱的,以色列并不是每天都发生爆炸,事实上在以色列死于车祸的人要比死于恐怖活动的更多。以色列人匆忙赚钱,享受生活,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不会受到动荡影响。生活有巨大的惯性,无论经历了大屠杀还是战乱,地震或者海啸,人都要过日子。
当然,以色列还是在我的眼前逐渐发生改变。要知道,我的年纪可是比这个国家还要老,我亲眼见证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诞生。有些改变我乐于拥抱,有些变化我不喜欢,但我想,我之所以不喜欢这些变化,可能只是因为我老了。
这种变化的感受,不只在以色列,还在中国。我九年前来北京,那个时候,街道上有好多人骑着自行车,三轮车也不少,现在这些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让人应接不暇的摩天大楼,那些小商店也找不到了,人们都去哪里了呢?
太多敌意,太少好奇
新京报:“人们都去哪里了呢?”这也是你的新书《乡村生活图景》想讲述的故事。这本书里有“乡愁”,也有古老以色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迷思,其中有一个故事《挖掘》,主题驳杂,既探讨了以色列人和土地的情感关联,也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彼此的信任危机,你怎么看待这个故事?
奥兹:我的小说不下判断,当我要评论或者判断时,我就去写散文或杂文。故事嘛,是多声部的,我在小说里不发声。当我写故事时,遭遇到彼此双方,我同时站在他们两边。当他们打架时,我还是同时站在他们两边,这就是一个作家该做的事情。如果必须要站队,那就成了一个政治家。
至于这个故事,从文本延展,我们的确可以联想到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许多阿拉伯村庄被夷为平地,以色列村庄代之拔地而起。在过去的60多年中,巴以双方一直因这块土地的所有权纷争不已。这一切犹如梦魇,令许多以色列人得不到安宁,令其感受到一种潜在的生存危机。他们之间互不信任,部分是因为无力想象对方:那种爱和恐惧,愤怒和激情。在巴以之间,有太多的敌意,太少的好奇。
新京报:就在不久前,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大会上悲哀地表示“巴以冲突”的和解遥遥无期,而且可能情况越来越糟糕。你觉得,为什么经过那么多年的痛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依然无法达成和解?
奥兹:我可以用一个词回答你:法西斯。双方都是这样的状态,他们需要所有的支持都在自己这里,自己百分之百正确,他者百分之百错误。但是我一直说,妥协是解决巴以冲突的唯一方法。
我是个懂得妥协的男人,不然我也不会和同一个女人保持56年的婚姻。妥协从来都不快乐,没有人会觉得妥协容易,它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成熟。现在巴以冲突看似很复杂,其实非常简单。以色列这个国家是这么狭小,小到中国人都无法想象。从特拉维夫开车到约旦不到一个小时,从耶路撒冷开车到巴勒斯坦地区只需要二十多分钟。
这样小的一块土地,它是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也应该是巴勒斯坦人的应许之地,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和平共处,融为一体呢?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成为一个欢乐的家庭呢?答案在于,他们不是“一个”,他们也不快乐,他们更不是“一家子”,他们是“不快乐的两个家庭”。不同的语言、历史、宗教信仰……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这所小房子划分成两个不同的单元,比邻而居。
我们需要把这所房子分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部分,以色列人得到A卧室,巴勒斯坦人得到B卧室,如果可能,厨房和客厅可以有一部分共享空间。如果不能做情人,就做邻居吧,希望有一天彼此都能邀请对方到家里来喝咖啡。我说得容易,其实很难,但总有一天会实现的,因为以色列人无处可去,巴勒斯坦人也是。在欧洲,不就是有个很小的捷克斯洛伐克吗?他们分成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相安无事,巴以问题应该以此为鉴。
幼稚的受害者情结
新京报:我想起了一本书,美国作家乔纳森·威尔森写的《巴勒斯坦之恋》,用一种新视角展现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看法,全书一个核心观点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能总把自己看做历史的受害者,他们也做了很多伤害阿拉伯人的事情。你看过这本书吗?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
奥兹:没看过这本书,但是听你说后,我准备回去看。人总是把自己当成受害者,这是普遍的人性。犹太人是受害者,女性是受害者,黑人是受害者,第三世界国家是受害者……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场“比赛谁比谁受伤害更多”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每个人都在说,“我比你更受伤害。”
即使在家庭内部,当婚姻触礁,兄弟阋墙,人们也总把自己当做受害者,把对方当成加害者,不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阿拉伯人也喜欢把自己当成无辜受害方,但双方都很幼稚。
我真的认为,在巴以冲突问题上,从来不该判决哪一方是好人还是坏人,双方都是受害者,也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侵略者。在以色列内部也形形色色,正统犹太教徒,犹太教改革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即使是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词,也不是一类人,而是好几类人的统称,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内部都是复国主义者,有的是资本家,有的信仰社会主义,有的是宗教狂热分子,有的甚至是法西斯,我并不是喜欢这个家族里所有的成员,而有些成员也以我为耻辱,这很正常,大家庭内部,这种矛盾司空见惯。但我们必须有一个共识:任何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家园,哪怕这个家园小得不能再小。
新京报:你的父亲来自俄国,母亲来自波兰,但这些大流散的犹太人,对于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寻找家园的问题,一直有迷惘。在你看来,从以色列建国至今,新一代以色列人是否已经成型?
奥兹:如果说真的有新一代以色列人成型的时候,就是所有人都随着同一首曲子翩翩起舞的时刻。但事实上,我并不希望这个时刻发生。我希望在我的国家,人们可以演奏不同的曲子,跳不同的舞蹈。有的曲子我喜欢,有的我讨厌,但是跳舞的时候有不同的曲调可以选择。就像在北京,可能有五千家餐厅,难道你希望有一天它变成同一家餐厅的连锁吗?点菜时服务生给你一张菜单,上面只有一道菜可供选择。天哪,那该有多无聊!我不会同意所有的见解,但我喜欢多样性,喜欢不同的曲调。
我们需要把这所房子分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部分,以色列人得到A卧室,巴勒斯坦人得到B卧室,如果可能,厨房和客厅可以有一部分共享空间。如果不能做情人,就做邻居吧,希望有一天彼此都能邀请对方到家里来喝咖啡。——奥兹
采写/新京报记者柏琳
奥兹:巴以两国如果做不了情人,就做邻居吧

|  |客服:0668-2886677QQ:75281068|大茂微博|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大茂名网
( 粤ICP备18149867号 )茂名市大茂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客服:0668-2886677QQ:75281068|大茂微博|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大茂名网
( 粤ICP备18149867号 )茂名市大茂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