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登陆,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用户注册

x
[作者按]:
六年前,王绍光教授撰《“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评“儒家宪政”》一文,对本人提出的“王道政治”理念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该文后在《开放时代》杂志发表,影响甚大。当时我撰写了《回应王绍光教授对“王道政治”与“儒教宪政”的批评》一文予以回应,但除英文稿收入《儒教宪政秩序》一书在海外公开发表外,中文稿一直未在国内公开发表。
六年后的今天,我捡出旧文,稍事润色,改为现在标题:《“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政治合法性的认定、贤士统治的理由与权力分配的正义》,授权澎湃新闻公开发表,以了一场学术公案也。
缘起
蒋庆:“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

2010年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了“儒教宪政与中国未来”国际学术会议。
本人《政治儒学》出版七年后,基于儒教“王道政治”之理念,本人又进一步提出了“儒教宪政”的构想。由于“王道”一词涉及“儒教中国”最根本的政治义理,而“宪政”一词又涉及现代国家最根本的制度安排,故受到国内外各种学派的批评质疑,其中最主要的批评质疑除来自自由主义外,还来自以王绍光教授为代表的新左派。
2010年5月3日至5日,由范瑞平教授与贝淡宁教授发起,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了“儒教宪政与中国未来”国际学术会议。在会议上,我提交了一系列关于“王道政治”与“儒教宪政”的主题论文供与会者讨论。会上自由主义学者与新左派学者对“王道政治”与“儒教宪政”提出了认真严肃且系统有据的批评,当时我一一作了口头回应。会后,我将数年来涉及“王道政治”与“儒教宪政”的文章结集为一书,名为《政治儒学·续篇:“王道政治”与“儒教宪政”——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儒学思考》。贝淡宁教授与范瑞平教授有心弘扬儒学,希望此书能在海外出英文版,好让世界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儒学,特别是了解中国大陆的“政治儒学”。在此书酝酿出版的过程中,书稿“评审委员会”希望本人对“王道政治”与“儒教宪政”的批评质疑再作一次系统全面的文字回应。
为此,我专门就王绍光教授的批评文章《“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评“儒家宪政”》一文进行了回应。至于回应是否如理,读者自会评判。嗟呼!今之所谓“回应”,古之所谓“辩”也。予岂好辩哉!孟子不得已而辩,荀子言君子必辩,予从二夫子后,亦不得已而辩也。
王绍光教授批评本人提出的“王道政治”理念与“儒教宪政”构想,涉及的问题很多,本人谨就其中五个最主要的问题再重申我的看法。
一、关于“合法性缺位”问题
首先,王教授用经验性的民意调查,来论证某一政治权力是否缺乏“政治合法性”。王教授认为,如果民意调查中民众对某一政府的满意度相当高,就证明某一政治权力具有充分而完备的“政治合法性”,即就不存在“合法性缺位”问题,因而批评我对中国近代以来“合法性缺位”的论断不准确。
对于这一问题,我要强调的是:我所说的“合法性缺位”是指“三重合法性缺位”,而不是指“一重合法性缺位”。即是指某一政治权力同时缺乏“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与“人心民意的合法性”,而不是指某一政治权力缺乏其中的某一种合法性。
在我看来,“超越神圣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宗教信仰与超验价值上的合法性。百年来的中国打倒了五千年来国人共同信仰的国民宗教——儒教,导致了中国的“政治合法性”不能建立在宗教信仰与超验价值上,即不能建立在儒教的“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上。而儒教在中国政治上的作用,正是为中国的政治权力提供“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即为中国的国家与政府提供神圣的宗教信仰与超验的道德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近代以来的中国存在“合法性缺位”,即是指存在“超越神圣合法性”缺位。也即是说,近代以来的中国,在科学崇拜与民主迷信的推动下,经过一次又一次世俗化的激进反宗教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国的儒教,使中国的政治不再能够体现神圣的宗教信仰与超验的道德价值,因而使中国的政治权力得不到“超越神圣合法性”的证成,最终造成了“超越神圣合法性”缺位的状况。
另外,在“历史文化合法性”问题上,尽管近年来中国文化传统开始受到国人重视,但相对于中国近代以来经过辛亥、“五四”、“文革”等一次高过一次的激烈反传统运动,特别是激烈反对所谓“封建专制”的运动,中国的政治传统在学理上成了完全负面的存在,从而在现实政治上被完全摧毁。也就是说,百年来无论哪一个中国的政治派别,无论其推崇何种主义,也无论属于左派还是右派,建立的政治架构在基本理念与根本制度上均是外来政治思想与政治模式的翻版,均缺乏源自中国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政治义理与政制形式,即均缺乏中国历史文化的自性特质。故在这一意义上,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权力仍然面临着另外一重“合法性缺位”问题,即仍然面临着“历史文化合法性”缺位问题。
至于“人心民意的合法性”,由于这一合法性是建立在主观、经验、感受上的合法性,故而这一合法性具有流动、短暂、变化的性质。只要政治权力能够使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与提高,在任何时代都能获得人心民意的认同,即形成所谓的“政绩合法性”。但是,“人心民意合法性”的内容很广泛,除物质生活的满足外,还包括各种基本权利的保障、民众的安全感与幸福感、民众对社会道德的评价与对政治公正的期待等,都是“人心民意合法性”的组成部分。因而完整的“人心民意合法性”,不应该只包括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应该包括上述各个方面的内容。
由此可见,王教授所理解的合法性,只局限于“人心民意的合法性”,而不涉及“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与“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在我看来,某一政治权力获得了“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即便是获得了完整的“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如果没有获得“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与“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这一政治权力在合法性上仍处于不完备的状态,这就是我所说的“合法性缺位”。前面已言,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权力大多缺乏“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与“历史文化的合法性”,所以存在着“合法性缺位”的问题。因此,就算如王教授所言某一政治权力拥有“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也不能否认我所说的中国近代以来存在着“合法性缺位”的问题。
此外,从王教授只从“人心民意”来理解合法性可以看出,王教授代表的左派与自由民主人士代表的右派在“政治合法性”上没有本质性的区别,二者都把“民意”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即二者都是近代西方“人民政治”的产物。只是左派自认为比右派具有更广泛的人民性,因而比右派具有更广泛的合法性,即左派更能代表大多数民众的意志,而右派则只代表少数大资产者的意志,因而右派与左派相比,无疑更缺乏广泛的合法性基础。
然而,王教授没有看到,其所坚持的左派立场,在合法性上却是与右派一样的立场——“民意合法性”立场,即所谓左派正是站在与右派相同的“民意合法性”立场上来反对右派,指责右派在合法性上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唯有自己才能真正代表民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其实左派与右派是一家,都是西方近代“人民政治”的产儿,即“现代性政治”的产儿,尽管这一家子人一百多年来相互争吵攻讦而不遗余力。
二、关于“规范合法性”与“认同合法性”问题
蒋庆:“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

蒋庆。
王教授为了否定我对西方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判断,通过经验性的问卷调查,说明西方民众对民主政府的信任度很底,因而证明西方民主政治不是“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而是“民意合法性”欠缺,即不是“过于民主”,而是“不够民主”。在这里,王教授没有看到“规范合法性”与“认同合法性”的区别,而是用“认同合法性”替换了“规范合法性”。
我们知道,西方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是“主权在民”。“主权在民”是一种建立在形而上学普遍原则上的“规范合法性”,是衡量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是否正当的理性标准,具有形上真理的规范性质。故不管现实政治中的民众对民主的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的主观认同度有多大,民主的合法性都是规范性的“主权在民”。极而言之,即使民主政治中的民众对民主的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都不认同,对民主政府的所作所为都不满意,民主政治的合法性仍然是“主权在民”。这是因为民主政治所具有的“主权在民”的“规范合法性”,是理性的、客观的、普遍的、恒定的,而对民主政府的认同则是经验的、主观的、心理的、流变的。
因此,“规范合法性”决定了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性质,是评判民主政治是否合法的根本标准,而不是主观心理的“认同合法性”决定了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性质,成为评判民主政治是否合法的根本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是指民主政治在“规范合法性”上只有一重,而缺乏另外两重“规范合法性”,即缺乏“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与“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因而在“规范合法性”上不受其它“规范合法性”的制约,即不受“超越神圣合法性”与“历史文化合法性”的制约。
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指出民主政治在合法性问题上存在着一重独大的严重弊端。王教授站在新左派“大民主”的立场上用主观心理的“认同合法性”来替换客观普遍的“规范合法性”,认为西方政治的问题不是由民主造成而是由不够民主造成,从而否定我对西方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论断。显然,这一做法不仅置换了“政治合法性”的不同概念——把“规范合法性”变成了“认同合法性”,也忽视了“主权在民”这一“规范合法性”在现代政治中所具有的普遍而绝对的统治地位——右派的“选民政治”与左派的“人民政治”只是“主权在民”的“规范合法性”在各自的意识形态中的不同表述。
另外,从王教授对“西方民主政治并不民主”的批评中也可以看到,左派与右派(自由民主派)虽然表面上水火不容,但在根本的政治思想上则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与一致性,即二者都高度推崇民主,二者的根本理念都肇始于近代西方“主权在民”的“政治现代性”,只是左派自认为比自由民主派更民主、更现代性而已。
三、关于文革的“大平等”与“儒教宪政”的“贤士统治”问题
王教授之所以被学界称为“新左派”,就是因为王教授对“文革”的“大平等”无限的怀念与推崇,认为中国理想的政治就是“文革”提出的消灭“三大差别”的绝对平等主义政治。这种政治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的全方位的彻底平等社会。因此,王教授特别反对“儒教宪政”提出的“贤士统治”的理念,即特别反对“儒教宪政”中通儒院的制度安排。在王教授看来,“儒教宪政”中体现“贤士统治”理念的通儒院,就是压制性的不平等的精英统治,所以必须反对。
确实,“儒教宪政”中的“贤士统治”无疑是一种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但这种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不是建立在王教授所说的资本对权力的垄断上,即不是建立在所谓“资产阶级法权”上,而是建立在人的德性与能力的自然差异上,即建立在现实中人的“贤”与“能”的天然合理的不平等上。孔子言“上智下愚不移”,孟子言“物之不齐物之情”,朱子言“天理之自然等差节文”,即是此义。亦即谓:政治儒学所理解的政治的不平等,是基于人的自然的不平等,故人的自然的不平等,是“贤士统治”的人性基础。因此,按照儒家“选贤举能”的根本原则,贤能者宜在高位。故“贤士统治”虽然不平等,但并非不公正,反而是一种“以不平等对待不平等”的自然的公正。
我们知道,政治权力是极为稀缺的资源,并非人人可以拥有。贤能之士因其德性与能力,在现实社会中处于与平庸大众不对等的地位,贤能之士因为这种不对等分配到更大的权力资源是天经地义之事,即是公正合理之事。因为政治权力具有公共性,是今人所说的“公共物品”,只有贤能之士的“贤”与“能”才能在根本的人格意义上保证政治权力的行使有效地做到为公不为私,而平庸大众因其在“贤”与“能”上的欠缺则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将政治权力分配给贤能之士与将政治权力分配给平庸大众,相比之下前者对贤能之士而言是公正的,后者对贤能之士而言是不公正的。这是因为,贤能之士所具有的仁心、德行、教养、信念、学识、智慧、才干使贤能之士应该在政治上分配到更大的权力,才能利用这一权力为民众服务。而平庸大众缺乏这种从政所必须的品质,而将权力平等地分配给平庸大众显然是对贤能之士的不公正——贤能之士应该得到权力却没有得到权力,因而不利于贤能之士利用权力治国平天下。
这里所说的公正,是一种“自然的公正”,即“天道秩序的公正”,亦即朱子“天理自然等差节文的公正”。人类的一切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这种公正,才称得上是“公正的制度”。也可以说,这种公正是孔子“正名”意义上的公正,柏拉图“各司其职”意义上的公正,亚里士多德“以不平等对待不平等”意义上的公正,伯克“自然贵族”意义上的公正。这种公正不是现代多元主义所推崇的“平面化不同”,而是人类所有古老智慧所肯定的“立体性等差”。总之,这是一种实质性的而非形式性的“分配的公正”,或者说“分配的正义”。(“公正”与“正义”乃翻译不同,词义相同,本文使用此词时随文各异,不求统一。)
其实,儒家与新左派亦有某些相近之处。儒家也反对王教授所反对的资本对权力的垄断与侵蚀,反对建立在“资产阶级法权”上的政治精英与财富精英合谋压榨广大民众,即反对王教授所说的打着民主旗号欺骗人的“金主政治”。但是,儒家不走极端,不会因为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虚伪与不平等就一刀切地扫除一切不平等,而不问这些不平等在“天道”秩序上是否具有合理性以及在历史延续中是否具有合法性,更不会如王教授一样纵情高歌“遍地英雄”、“六亿舜尧”的“文革”式“彻底大平等政治”,而是主张以建立在“贤”与“能”上的合理的等级性“贤士统治”,取代建立在资本与强权合谋上的不合理的压迫性“金权统治”,从而以“贤士统治”所推崇的“王道”与“仁政”来保护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这是因为在儒家看来,只有儒家的“贤能之士”因其道德品性、智慧学识与从政能力才能真正实质性地代表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因而在“贤能之士”获得统治权力后才能强有力地反对资本对权力的垄断侵蚀,即才能强有力地反对政治精英与财富精英合谋对广大民众的压榨剝夺。
因此,王教授不应担心“儒教宪政”所体现的“贤士统治”理念,更不必顾虑通儒院实现“贤士统治”的制度安排,因为历史昭示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代表民众利益为民请命的都是儒家的贤能士大夫!是故,儒家贤士在德性、品行、信念、学识、教养、能力、身份上的自我认同,在人格上的道德期许以及在历史中的道统传承,都决定了贤士不是民众的压迫者,而是民众根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与追求者。这一点看看《论语》、《孟子》、《礼记·儒行篇》、横渠“四句教”、王阳明奏议以及历代史书就会知道。我们说儒家贤士代表了民众的根本利益,但这种“代表”是柏克所说的“实质性代表”,而不是现代民主政治中的“程序性代表”,两种“代表”相比,“实质性代表”比“程序性代表”更可靠,因为“程序性代表”未必真能“代表”,而“实质性代表”则是已经“代表”,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否定“程序性代表”的正面价值。此外,儒家贤士在“三代”后的“无王时代”代表王道,王道有“人心民意合法性”一重,故代表民众正当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正是贤士之所以为贤士的神圣天职。
所以,王教授推崇的“文革大平等”,按照王教授的术语来说,不是历史中可能实现的“现实的乌托邦”,而儒教的“贤士统治”才是历史中可能实现的“现实的乌托邦”。这是因为,儒教的“贤士统治”在中国古代曾经实现过,今天则可以继承其精神因应时代条件的变化再造创性地实现之。而“文革”中“消灭三大差别”的“大平等”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实现,只能是名符其实的“空想的乌托邦”,尽管我们对这种“空想的乌托邦”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抱着深深的同情与敬意。
也即是说,在不远的将来,通过“儒教宪政”制度的重建,如通过议会中通儒院的制度安排,将一部分政治权力,即一部分议会权力,给予信奉儒家价值的儒士共同体成员并非不可能。而彻底消灭社会分工将劳心者与劳力者一体拉平的做法则绝对不可能!我们今天可以设想让王教授去东莞工厂的流水线上打工,而让东莞工厂的打工仔到王教授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讲台上当教授吗?这可是“文革”中“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大平等”理想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是故,王教授的“大平等”左派理想注定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空想,而“儒教宪政”的“贤士统治”则是可以在历史中期待、转化、创造与实现的儒家理想!
在平等问题上,与在主权问题与民意问题上一样,左派与自由民主派也具有同质性与一致性,即两派均反对“等级性政治”,均追求“平等性政治”。左派追求的是“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平等政治,自由民主派追求的是“一人一票参与选举”的平等政治,二者都把“等级性政治”斥为“封建专制”加以反对,因而二者都反对儒教的“贤士统治”。然而,左派认为,自由民主派追求的平等政治因为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不是真正的平等政治,反而掩盖了现实政治中的不平等,即以形式的平等掩盖了实质的不平等,而左派追求的平等政治因为消灭了“资产阶级法权”,因而才是真正的实质性的平等。
不过,站在儒家的立场来看,左派批评右派的不平等,正是站在与右派一样的“政治现代性”立场来批评右派,因为追求“平等性政治”乃是西方近代以来“政治现代性”最重要的特质。而今天的所谓左派右派,无论其如何相互攻击,均是“一母二子”,即均是“政治现代性”最忠实的产儿。只不过,左派比右派更忠实于其母,即更忠实于“政治现代性”。左派在追求平等上远非右派可及,因为左派追求的平等要比右派追求的平等平等得多得多,即在追求“平等性政治”上左派比右派更平等。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左派与右派都反对儒教的“贤士统治”,而左派的反对却要比右派的反对激烈得多。
是故,就王教授对本人“儒教宪政”构想中“贤士统治”的批评,亦应作如是观。
四、关于权力分配的正义问题
蒋庆:“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

由上分析可知,其实新左派与自由民主派有极为相同之处,即都追求政治价值上的平等主义与民主主义,并由这种平等主义与民主主义推导出政治权力的平等分配制度。只是新左派认为自由民主主义“一人一票”的权力分配制度不够平等不够民主,因而主张民众在政治上应最大限度地全面参与政治过程,并通过“大平等”与“大民主”掌握更大的政治权力。
然而,对这一建立在平等主义与民主主义上的关于权力分配的政治义理与制度安排,根据儒家“王道政治”的理念与“儒教宪政”的构想,必须回答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上涉及到的“分配正义”的四个根本问题:
1、人类现实的存在中是否存在着政治意义上的凡圣贤不肖之别?
2、如果人类现实的存在中存在着政治意义上的凡圣贤不肖之别,这种凡圣贤不肖之别是否具有权力分配上的政治意义?
3、如果凡圣贤不肖之别具有权力分配上的政治意义,这种政治上的权力分配是否符合正义?
4、如果凡圣贤不肖之别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上向圣贤倾斜符合正义,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合理有效地保障这种政治权力的分配向圣贤倾斜的正义?
对这四个根本政治问题的回答,新左派的看法与自由民主派并无本质区别:第一,人类经过启蒙后,人人都敢于在公共领域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即每个人在理性上都已经达到了完全的自主与自义,实现了“承认的政治”,即实现了人人平等的政治,故在人类现实的存在中已不存在政治意义上的凡圣贤不肖之别;第二,由于人类现实的存在中已不存在政治意义上的凡圣贤不肖之别,就不存在凡圣贤不肖之别在权力分配上的政治意义问题;第三,由于不存在凡圣贤不肖之别在权力分配上的政治意义问题,就不存在政治上权力分配向圣贤倾斜的正义问题;第四,由于不存在凡圣贤不肖之别在政治权力分配上向圣贤倾斜的正义问题,就不存在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有效保障政治权力的分配向圣贤倾斜的正义问题。
然而,对这四个根本政治问题的回答,政治儒学与新左派及自由民主派的看法正好相反:人类的启蒙只是表面性的,并且是解构道德的,启蒙后的人类在道德上或者说在普遍的善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提升与进步。人人都敢于在公共领域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并达到完全的自主与自义,只能说明人对超越神圣的价值与崇高绝对的道德表现出愚昧无知与狂妄自大。所谓人人平等的“承认的政治”也只是与上帝争平等的政治(西方),或者说与圣贤争平等的政治(中国),这种政治无疑是“自义”与“自圣”的“人人是神是圣的政治”,儒家坚决反对这种人人平等的既愚昧无知又狂妄自大的政治。
是故,在政治儒学看来,第一,人类现实中永远都会存在着政治意义上的凡圣贤不肖之别;第二,这种凡圣贤不肖之别具有权力分配上的政治意义;第三,这种凡圣贤不肖之别具有权力分配上的政治意义,即符合“以不平等对待不平等”以及符合“以他人应得之物给予应得者”的政治权力向圣贤倾斜的“权力分配的正义”;第四,政治权力向圣贤倾斜的“权力分配的正义”必须建立合理的制度安排即宪政制度才能有效保障政治权力的分配向圣贤倾斜而不是向凡庸不肖倾斜,而这样的制度才是“正义的制度”。
正是基于这四个理由,本人提出了建立在“王道政治”理念上的“儒教宪政”构想。这一构想的目的说白了就是要通过建立符合儒家根本政治价值——王道——的制度安排,即通过符合儒教根本义理的宪政制度有效地保障政治权力的分配向圣贤倾斜,以此实现政治权力上的分配正义,从而使人类现实中存在着的凡圣贤不肖之别具有政治权力分配上的义理意义与制度意义。这就是政治儒学推崇具有所谓精英政治意味的“贤士统治”的理由。只是儒教的精英不是现代社会中只握有学科知识与专业技术的“世俗精英”,即不是韦伯所说的缺乏信仰追求与精神关怀的现代“无灵魂的专家”,而是证悟“天道”、上达“天德”、下传“天意”、践行“天命”的圣贤君子,即是信奉超越神圣价值、深谙圣贤经典、富于古典教养、具有从政德行与从政能力的“横渠四句教”意义上的贤士精英。
当然,贤士精英为治理好国家,也必须掌握治理国家所必须的学科知识与专业技术,并且应该掌握得更好,即“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职是之故,鉴于新左派的政治主张是比自由民主派更平等更民主的“大平等”与“大民主”的政治主张,所以作为新左派主力的王教授激烈反对本人的“政治儒学”以及激烈反对本人建立在儒家“王道政治”上的“贤士统治”与“儒教宪政”构想,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政治儒学”主张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上向圣贤倾斜的“分配正义”体现了人类“等级性政治”的古典原则,直接否定了新左派“大平等”与“大民主”的现代性理想,故“政治儒学”遭到王教授比批判自由主义更猛烈更激忿的批判,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五、关于王绍光教授所说的“好东西”
王教授的文章通篇都是在批评“儒教宪政”不是“好东西”,那么,什么是王教授所说的“好东西”呢?在王教授文章的结尾处,他提出了自己替代“儒教宪政”的“好东西”:“中华社会主义民主”。王教授借用“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的义理架构指出:社会主义是天道(超越神圣的合法性),民主是人道(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中华是地道(历史文化的合法性)。
在这里,王教授对天道(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解。依儒教,作为超越神圣合法性的天道,指涉的是宗教性的超越神圣价值或超验形上本体,是信仰把握的对象而不是理性知解的对象。而左派所依据的理论是生命的无神论与历史的物质论,亦即是建立在启蒙理性上的历史进步论与科技至上论。这种理论否定了对超越神圣的“昊天上帝”的信仰与先验形上的“天道天命”的信仰,而是相信辨证理性能够创造出一个未来合理(合乎理性)的新世界,并相信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这种体现“政治现代性”特质的世俗的、理性的、启蒙的、科学的、技术的、无神的、物质的左派理论,显然不能等同于儒教“三重合法性”中关于“超越神圣合法性”的理论。因为儒教中“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就是“昊天上帝的合法性”,而左派理论没有这种超越神圣的宗教性质,因而不会具有“超越神圣的合法性”。
至于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方面,王教授认为民主是人道。这没有错,但“民主”所体现的大众参与不能作为政治上唯一的“规范合法性”,即不能以大众参与作为政治权力是否正当的唯一标准。鉴于民主属于人道,建立在“王道政治”上的“儒教宪政”有“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一重,故“儒教宪政”并不排斥合理的大众参与。大众参与在“儒教宪政”的制度安排中,即在儒教“议会三院制”的庶民院中,得到了制度性的合理安排,获得了宪政性的有力保障。但这种大众参与是代议制意义上的大众参与,而不是王教授推崇的“文革式大民主”意义上的大众参与。
蒋庆:“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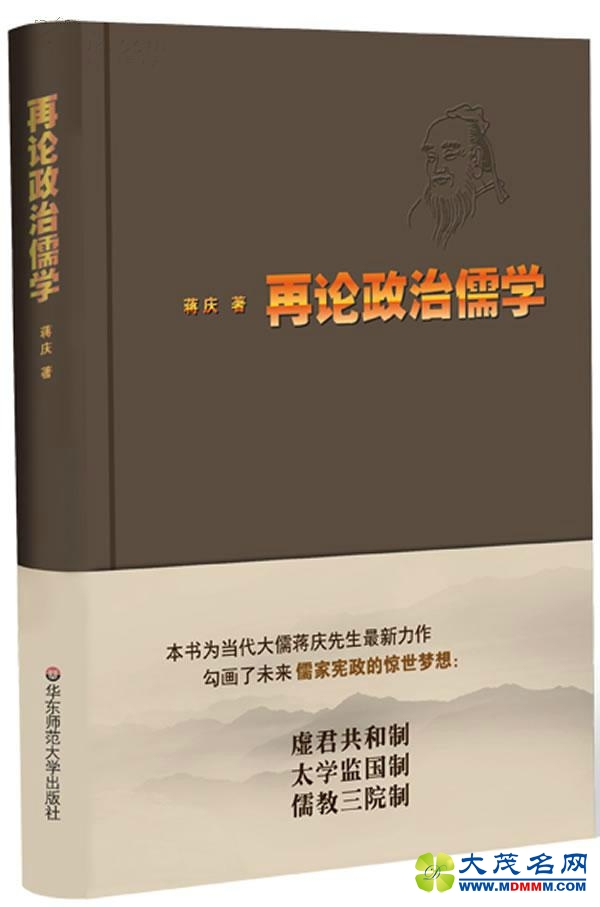
但是,尽管如此,“儒教宪政”在本质上则是精英政治,即是一种贤能之士应当握有更大权力的精英政治(如果可以借用西方“精英政治”一词的话),庶民院的制度安排不会改变“儒教宪政”这一独特的精英政治即“贤士统治”的性质。正是在这一点上,王教授认为“儒教宪政”是精英政治,大致看到了儒教政治的核心,即儒教政治是合理的“等级性政治”。
但是,王教授文章中却把现代西方大资产者占有议会政治权力称为精英政治,这显然与“儒教宪政”的精英政治不同:前者占有权力是基于金钱财产,后者拥有权力是基于德能学识。(基于金钱财产的政治形态不仅是西方政治的现代形态,也是西方政治的传统形态。在西方的历史中,古希腊的政治形态与古罗马的政治形态中即存在着这种基于金钱财产的政治形态。而基于德能学识的政治形态不只是今日中国重建“儒教宪政”的义理诉求,也是“儒教中国”五千年历史中一脉相承的“德治传统”与“学治传统”。此义详参本人《再论政治儒学》一书中的《太学五学说》。)
因此,如果按照“政治儒学”关于“贤士统治”的精英理论,王教授所说的占有议会政治权力的大资产者并非真正的精英,而可能是庸众,甚至可能是“乐得其欲”的小人。因为儒家的精英如前所述是证悟“天道”、上达“天德”、下传“天意”、践行“天命”的“圣贤君子”,即是信奉超越神圣价值、深谙圣贤经典、富于古典教养、具有从政德行与从政能力的“横渠四句教”意义上的“贤士精英”,而不是巨额金钱财产的所有者。《礼记》言:“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即是此义。
至于王教授认为中华是地道,即是“历史文化的合法性”,理解准确,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总之,出于人类普遍的良知与儒家“民胞物与”的仁心,我敬重新左派对弱势大众的同情关怀。但出于儒家的义理立场,我不接受新左派“大平等”与“大民主”的主张。因为在我看来,对弱势大众的同情关怀不是属于政治上的“正义”问题,而是属于宗教上的“仁爱”问题,故同情关怀弱势大众的“仁爱”与权力分配向贤士君子倾斜的“正义”是两回事。因此,儒家贤士君子若能在宪政制度中分配到更大的政治权力,则意味着更有利于实现儒家基于同情仁爱之心的“仁政”,从而更有利于在国家立法与制定政策上关怀弱势大众,因为仁民爱物的恻隐之心正是贤士君子之所以为贤士君子的根本特征。正因为如此,孔子才认为执政者必须具有“仁”德,孟子才说“仁者宜在高位”,阳明先生才说士大夫必须具有“良知”。
另外,我们今日反思民主政治的历史与现状,自由民主的“政治现代性”已经在平等与民主上出现了很多问题。而新左派的“大平等”与“大民主”主张又企图继续沿着这一“政治现代性”的道路,用更现代性的方案来解决“政治现代性”带来的危机,即把“政治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如理性、启蒙、自主、自由、平等、权利、民主等推到极端来反对“政治现代性”。这一做法实质上是对“政治现代性”的传承、发展、完善与新的证成。对于新左派这种以“政治现代性”原则来解决“政治现代性”问题的方案,我是看不到希望的。
是故,关于“政治现代性”问题,只能用“政治传统性”来对治,因为在看不到希望时,回归传统就是唯一的希望。就中国而言,回归传统就是回归儒教文明,“儒教宪政”就是回归儒教文明在政治重建上的制度性诉求。这一诉求既区别于中国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也区别于中国的新左派,当然也区别于中国的港台新儒家,而是一种建构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色即儒家文化特色的中国式政治制度的诉求。
以上就是我对王教授批评“王道政治”与“儒教宪政”的五个方面的回应。王教授的批评文章名为《“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我的上述回应可以用王教授文章的语式来回答:“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只是把问号换成了句号而已。
蒋庆:“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

|  |客服:0668-2886677QQ:75281068|大茂微博|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大茂名网
( 粤ICP备18149867号 )茂名市大茂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客服:0668-2886677QQ:75281068|大茂微博|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大茂名网
( 粤ICP备18149867号 )茂名市大茂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