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季 第3集 关于粉(一)
关于粉,这个名词与小姐一样,被社会异化了。
鳌头、袂花、羊角一带青年的父辈母辈早些年,都会用人工磨坊磨蒸出那些用大米、红薯淀粉、绿豆淀粉、马铃薯淀粉、蚕豆淀粉等作材料的粉条。只是我还记得大约96年,在十二中的宿舍就有一名外来男子吸白粉过量猝死;2004年在嘉燕大酒店夜总会的包厢里,在霹雳火的包厢里,2005年在翡翠明珠的包厢里,在火车东站地下的欢乐今宵大厅里,我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女孩用卡片把碟子里的粉末往鼻子里送的时候,我相信,那些还生活在黄土地,每日披星戴月劳作的父辈们,他们一辈子也不想再做什么人工粉了。
所以,我们在市区,很少能吃到正宗的人工粉皮了。
小时候,在红旗电影院门前那条街上,一棵大树菠萝下的位置处,有一摊炒粉,老板是一名中农(中年农民),很朴实的样子,他的粉充满矛盾,既弹牙又柔软,既有豆香又没有过分的豆卤味,他的粉皮装在大竹箩筐里,根据客人的需要,把大片的粉皮放在砧板上,用锋利的竹片均匀划开。两个竹筐之间,放着一个柴炉,尤加利树的干柴烧起来很有火力,那薄薄的铁锅,香油在跳跃,不多时,一碟香喷喷的炒粉立刻完成,食客有坐在小板凳上,有蹲在树荫下,有站着,没有什么阶级矛盾。
那时候,没有地沟油,没有漂白剂,没有城管,也没有收保护费的临时工。
我也还没有把忧伤、惆怅、孤苦、寂寞、空虚收集转载在骨髓里,那些年,五毛钱可以吃到饱。2毛钱可以在大笨象公园的工人电影院看《李小龙》。
如今,狗肉店的机制捞粉,都10块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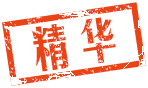

 |客服:0668-2886677QQ:75281068|大茂微博|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大茂名网
( 粤ICP备18149867号 )茂名市大茂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客服:0668-2886677QQ:75281068|大茂微博|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大茂名网
( 粤ICP备18149867号 )茂名市大茂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