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马上注册登陆,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用户注册

x
“通敌”还是“合作”:抗战史研究可以去道德化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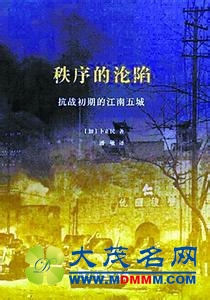
“通敌”还是“合作”?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历史经验,应置于纵、横两个坐标轴上加以审视。所谓横的坐标轴,即在二战史的背景中平行比较。而纵的坐标轴,即将此问题嵌入中国自身的思想脉络中,联系易代之际的历史抉择,尤其是面临异族入侵时士庶的应对策略,在这一抵抗与妥协的传统中反思沦陷区的历史经验。
《秩序的沦陷》意在跳脱民族国家的框架,以二战史研究中的合作史(historiography of collaboration)为参照系,在区域史的范围内呈现战时中国的“灰色地带”(gray zone)。此书的长处是取自下而上的视角,兼具世界史的背景;而其不足之处或是因标举价值中立,将政治秩序与道德意识剥离开后,对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与情感记忆体贴不够。
卜正民(Timothy Brook)这本书的主题词是collaboration,书中译为“合作”,更通行的译法是“通敌”。原书题为Collaboration: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台译本的书名较忠实于原著,译作《通敌:二战中国的日本特务与地方菁英》(林添贵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15)。大陆版在标题上做了较大的改动,几乎是另取了一个书名《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更改标题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普通读者或许不会计较,但对研究者而言,商务版的书名虽点出时空范围,却掩盖了正标题“Collaboration”一词背后的学术史脉络,即作者在第一章中梳理的“合作史”。
“秩序的沦陷”似有歧义,该书的主眼不在“沦陷”,而在“占领”之后的秩序重建:“外国占领对一个社会的惯常结构造成了极大的、残酷的侵扰和中断”,“它破坏了集体生活的网络和日常生活规范,而且使社会团体和个人在这种环境下面临着危险的选择”,占领之后最迫切的任务是打造基层组织,“建立新政治秩序”(60页)。
卜正民对“collaboration”的定义是:“在占领当局的监督和施压下,继续行使权力。”他在书中抱怨说,按此定义,“很难找到一个精确的中文对应词”(17页)。确实较之欧美相对成熟的合作史研究,“中文缺少对collaboration一词的讨论”,无论是狭义的“通敌”,或是泛化的“合作”。但中文中与collaboration对应——至少是模糊对应的词,并不限于“合作”、“通敌”,还有“事伪”、“附逆”、“落水”等。不过或许在作者看来,“通敌”之“敌”、“事伪”之“伪”、“附逆”之“逆”,都预设了政治立场与道德判断,不如“合作”一词显得价值中立。但在“沦陷”的特殊语境中,是否能超然于敌我对峙,持第三方的立场?用“合作”或更轻描淡写的“一起工作”替换“附逆”、“事伪”、“通敌”,摘掉“汉奸”的帽子改称“合作者”,能否保证价值中立呢?
更极端地说,在“沦陷”的问题上,没有中立的概念工具,只有伪装中立的语词。译者在序中坦言,翻译过程并不轻松,仅仅“collaboration”一词就让他大为头疼。“其实collaboration最接近汉语的‘勾结’一词,但‘勾结’这个词又太具有感情色彩,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带有这样的感情色彩不免让人读起来不太舒畅。”因此collaboration一词在书中的译法极不稳定,时而译为“合作”,时而译为“通敌”,时而译为“勾结”,时而译为“一起工作”。在我看来,与其刻意抹去语词自带的情感色彩,不如正视“汉奸”、“附逆”、“事伪”这些词背后的历史记忆。沦陷区研究所追求的价值中立,并不等于斩断历史的尾巴,将积淀在语词中的道德情感排斥在外。
眼光向下
“如果我们向下看那些模糊不清的灌木丛,而不是向上看熟悉的通敌或抵抗的大树,我们更有可能理解与日本人一起工作的中国人。”(275页)“灌木丛”在这里指代的是“大树”阴影下的地方社会(local society)。欧美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研究,大致分成两路:一路“向上看”,关注沦陷区的傀儡政权,以汪伪政权为代表,即卜正民所说的“大树”;另一路则眼光向下,搜寻沦陷区的地方经验。前者偏向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后者侧重于社会史、文化史。《秩序的沦陷》以抗战初期的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为个案,自然属于后一种研究路数。
区域史的视角,并不限于沦陷区研究,其实是欧美学者处理战时中国的基本范式(参看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1937-1945)。卜正民在探索“灌木丛”的同时也不忘仰望“通敌”的“大树”,除了江南地区的占领机构,他还处理过1938年“华中维新政府”的创立过程(The Creation of the Reformed Government in Central China)。
撇开上层的意识形态纷争,从底层透视沦陷初期的社会状况,将“合作”转化为有待研究的课题,是卜正民此书的基本方法。着眼于战时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关系网络及道德真空,这一“向下看”的研究取径,与日本明清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论”颇有相通之处。所谓“地域社会论”,一方面以“秩序稀少性”的感受为前提,另一方面试图追问非常态下秩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对这种研究方法有一段相当漂亮的概括:
看起来好像是在处理和大局无关的细微琐事。然而它所关心的却不一定仅仅止于个别的微观情事。从许多被认为属于“地域社会论”的研究中可以感受到的旨趣其实是要从这些事例中抽离出当时人的行为型态、抉择的依据,以及社会面向等,以整合性的概念模式来把握,甚至从普遍性的脉络里捕捉。关键不在问题的大小,而在问题的方向性。不是像神一般高高在上,以超然性观察立场来俯瞰这个社会,而是由社会中各个角落来选择个别的人群行动,这些行动才是了解社会的真正本质。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思考人们为何这样地活动时,问题的方向性势必是从人们的行为与动机出发,成为一种微观的、由下而上的研究取径。(何淑宜译《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十七世纪中国的秩序问题》序言)
日本“地域社会论”主要以明清之际的江南社会为考察范围,因为按倡导者森正夫的说法,长江三角洲自宋以来便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经济带或“先进地带”。但“地域社会”在日本明清史研究中不仅是作为实体的概念使用,而从作为实体的地域性框架中提升出某种特定的方法论立场(森正夫《中国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视角》)。如岸本美绪所言,“地域社会论”关注当时人为何采取这样的行动,并试图揭示每个人所谓合理的利害计算,与超越一己私利的集体意识、道德观念是纠缠在一起的。
地方史的视角让研究者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个人做出选择的历史情境上。台湾学者罗久蓉即以1941年郑州维持会为主要案例,利用光复后的审讯记录,分别从动机、人事背景、行为三方面考察抗战时期“汉奸”的成因。郑州商民参与维持会的经验显示,人际关系网络在与日伪合作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不能将通敌行为从历史情境中抽离出来,而应在沦陷时间的久暂、地方经济生态、权力运作机制等脉络下反思“汉奸”的定义与成因。卜正民此书同样提醒我们历史人物尤其是小人物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是否通敌涉及个人在面对战争的威胁时所具备的心理成熟程度,个人在面对由于权力带来的意外收获时的贪婪程度,或者个人在面对其他权力竞争者时的应变能力。不认真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去谴责这些人贪婪或叛国,是再造他们被迫通敌的政治土壤:假定每个人都进行了抵抗,将抗战剧演成了传奇剧。(283页)
面目不清的地方社会
“江南五城”在沦陷下并非一个不言自明的地域概念。为何选择“江南”这片地区,为何考察这五个城镇,除了材料的限制外,不可忽视战争状态下地域概念的政治性。福柯在《权力的地理学》中指出地域概念与战略术语之间的借用关系,因为地理学就是在军事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地图上的分界线,看似确定不移,其实是各种政治、外交势力乃至军事势力折冲的结果。若从词源上追溯,地理学上的“地区”(region)由“指挥”(regere)演变而来,就是军事区域;作为行政区划的“省份”,从“战胜”(vincere)转化过来,原意是一片被占领的土地(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是以军事占领为前提,因日方分而治之的侵华政策而形成的“非自然”的地域范畴。
“地方的近代史”这两年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单就“近代”这一时段而言,我们对“地方”的了解多是浮于表面的。如王汎森所言,静默的地方社会中有一套无所不在的“传讯机制”,“道德镇守使”便是这无声世界的维护者(《“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对“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六期)。严格地说,《秩序的沦陷》对抗战初期地方社会的把握仍是浅层次的,虽拎出了几个活跃的投机分子及面目模糊的“头面人物”,但读者更期待看到战时地方社会的“传讯机制”是如何运作的,谁充当了这个无声社会的维护者或破坏者?不妨进一步追问,近代以来随着士绅阶层的破产、知识菁英的流失,地方社会是否还有自己的“道德镇守使”?
卜正民笔下的“地方菁英”,绝非基层社会的“道德镇守使”,而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此类人的共同特征是:庇护网络、经纪人技能及与地方社会的广泛联系。在占领者与地方社会的权力博弈中,卜正民发现越到基层,日本军方及特务机构越不能完全控制局面,在处理具体事务时不得不依赖“地方头面人物”。掌握地方资源及关系网的投机分子,抓住占领者抛出的橄榄枝,让形势朝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沦陷初期“自治委员会”成员在日后的改组中还能成功保住自己的职位,即显示出基层体系的适应能力。但投机者的适应性决不可混同于易代之际地方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后者以士绅阶层为主导。卜正民以为基层社会的政治事件,都发生在社会网络和组织之间,卷入其中者都参与到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中。每次政治事件均在实际利益层面上运作,总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意味着事件本身的政治色彩可能遭到底层的漠视乃至削弱。
抗战初期日本占领机构与地方投机分子之间的寄生关系,在卜正民看来,暗合了杜赞奇提出的“内卷化”概念:“与政权正式结构相伴随的是非正式结构的出现,比如赢利型经纪人。”(《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依赖非正式结构介入地方治理,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为国家政权是以内卷化的方式发展,在基层社会,非正式群体变成了无法控制的力量,并代替了传统地方政府的管理”(272页)。借用“内卷化”的概念来解释抗战初期江南地区的权力结构,似忽略了华北与华中、农村与城镇的地域差异。从诸多关于明清之际江南社会的研究成果来看,不难想象抗战在此地唤起的民间记忆包括抵抗与妥协两方面的传统。卜正民此书对地方社会的刻画之所以流于表层,除了材料的制约,最大的原因是没有着力发掘江南特有的文化地层,藉以展现地方传统的延续或断裂。
“模糊化”之后?
二战史中的“合作史”研究,意在破除抵抗的“神话”。打破“神话”的利器,不外乎强调:动机的模糊性、结局的不可知。卜正民声称史学家有责任去挖掘浅层次阅读中一些由于文化所确立的道德准则而被忽略的“模棱两可”的东西。模棱两可意味着:
我们不能根据我们强加的道德要求来推断处于仓促条件下人们行动的原因,亦不能仅仅根据参与者不能预测的结果来评估他们的行为。让历史行动远离被民族主义束缚的假想,或远离使其老掉牙的道德预设,使事件退回到无法预料的不确定状态。(285页)
“模糊性”或“暧昧性”(ambiguity)似乎成了“合作史”研究的价值落脚点。民族主义者将沦陷区视为两种人——坚决的抵抗者与同样坚决的妥协者的战场,欧美学者试图修正过于黑白分明的历史图景,着眼于抵抗与妥协之间的“灰色地带”,展现个体选择的复杂性。
“灰色地带”(gray zone)的说法,来自普里奥·莱维(Primo Levi),一位犹太裔化学家对纳粹集中营的描述。作为亲历者,莱维指出在易于辨识的善与恶、无条件的抵抗与无原则的妥协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一大片模糊的中间地带,有许多挣扎着活下去、已经妥协、随时准备妥协,或还没来得及妥协的灰色人物。集中营就像一个人性的实验室,其中人和人的关系不能简单划分成受害者与迫害者两个阵营,事实上盟友中亦藏有敌人,敌人中未必没有潜在的盟友,谁也辨识不出一条清晰的边界,说这边是正义的,那边是堕落的,而更接近于霍布斯所谓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谁有资格审判这些灰色人物?莱维以为,或许只有经历过集中营的人性测验,知道处于生存高压下究竟意味着什么的人,才可能做出忠恕的评断。
以“模糊性”为旨归,有时距道德相对主义只有一步之遥。卜正民坚称“历史研究者不能塑造道德标准,也不能制造道德知识”(history does not fashion moral subjects, nor produce moral knowledge)。而中国自身的史学传统,正是把史著当作伦理教科书,旨在“塑造道德标准”、“制造道德知识”。作者随后说“历史研究者的任务不是提出错误的观点来抨击过去的历史参与者或现在的读者,而是调查在某时某地产生道德准则的标准和条件以便进行研究”(281页)。《秩序的沦陷》却搁置了道德判断,引进“合作史”的视野,并未深入“调查在某时某地产生道德准则的标准和条件”。
卜正民有意从“非道德”的角度来解释“合作”政治,他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透过人为设置的道德框架,审视其背后的政治现实。但也坦言在写作过程中没办法将道德和政治完全剥离开来,“因为尽管它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起作用,却常常以相同的语言表达来展开”(12页)。
“去道德化”的陷阱,在讨论占领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时体现得格外明显。卜正民首先承认日军的存在是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随后又亮出一个刺目的观点:“没有一个政权与生俱来是种族、文化和政治的产物。”换言之,“所有的政权都依赖宣传打造”(all states rely on fictions)。“去道德化”的现实政治,便是没有真伪之别的政治:“有些是以温和平静的方式,有些是以残忍凶猛的方式,来掩盖该政权必然的不足,掩盖其与外部利益的妥协,掩盖其依赖于高压政治强迫民众接受某种民族认同”(255页)。如果消解民族国家的建构,摆脱道德框架的束缚,得到的是这样暧昧的结论,那研究者还不如戴着镣铐跳舞。
“通敌”还是“合作”:抗战史研究可以去道德化么?

|
|
 |客服:0668-2886677QQ:75281068|大茂微博|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大茂名网
( 粤ICP备18149867号 )茂名市大茂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客服:0668-2886677QQ:75281068|大茂微博|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大茂名网
( 粤ICP备18149867号 )茂名市大茂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