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登陆,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用户注册

x
活在真人秀里

Photo by Johan Warden/Gallery Stock
临床精神医学领域的论文很少能在学术期刊以外的媒体上掀起波澜,不过一篇名为《“楚门妄想症“:全球化时代的精神病》的论文(译注:病名源于电影《楚门的世界》)得到全世界的关注似乎也没什么奇怪的。论文作者乔尔·古尔德和伊安·古尔德兄弟(Joel and Ian Gold)展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病例,患者都深信有人正在偷偷地拍摄他们的生活,并在电视上作为真人秀播出。
其中一个病例的患者去了纽约,要求与拍摄他生活的节目“导演”见面,并且希望确认世贸大厦被撞毁是真实事件还是节目方为他好而杜撰的情节。另一病例中,一位曾经由于躁狂发作(manic episode)而住进医院的记者认为自己经历的治疗情节是伪造的,一旦真相大白,他就会因为报道这一故事而获新闻奖。另一个患者则真的是真人秀剧组里的员工,他开始觉得剧组同事在偷偷地拍摄他,并且经常期待摄像机一下子转向他的那一刻——让所有人明白他才是这个节目中真正的明星。
评论者大多同意:被诊断为精神分裂或者躁郁症(bipolar disorder),并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这些病例,其实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它暴露了我们整个文化中的一处病灶。它们被看作是这一现代社会痼疾的极端例子:我们对成名的深深着迷,让我们变成了在个人天地里自我陶醉的明星。无孔不入的媒体文化扭曲了我们的现实意识,模糊了生活事实与虚构故事之间的界线。我们对现实的体验仿佛被修剪过的草坪,又像是私人定制的商品,从垃圾邮件到搜索引擎,我们生活中的各种事物都谨慎地怂恿着我们,让我们相信自己便是宇宙的中心。而那些病例似乎完美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精神,成了当今时代的警世寓言。
活在真人秀里

躁郁症(bipolar disorder)
“楚门妄想症”与当今时代出奇地契合,部分是因为时不时会有好莱坞大片根据偏执妄想症的病历记录和临床文献,改编出电视剧情。流行文化圈热门的创作主题,要么是与暗中监视和精神控制有关的科幻技术,要么是由虚拟场景和植入记忆虚构的模拟现实,剧中人只有在错乱的梦境序列中,或者当虚拟世界的面具不慎滑落时,才能一瞥现实的真相。几十年前,这类构思造就的是那些疯癫的银幕形象,多半是杀人狂之流。现在则会刻画出像金·凯利(Jim Carrey)饰演的“楚门”那样的角色,后者确确实实卷入了精心安排的秘密中,而他身边的人都假装不知情。这些故事明显呼应了我们浸淫于技术的现代生活。直到近来,我们还在猜测为什么人们如此乐意接受这些将现实彻底疏离的剧情。这说明媒体技术正在把所有人都变成妄想狂吗?还是说那些离奇妄想比以前更能让人理解了?
活在真人秀里

第一个对新兴科技与精神疾病症状之间奇特的共生现象进行研究的,是维克托·托斯克(Victor Tausk),他是弗洛伊德的早期门徒。1919年,他发表论文提出了他称为“摄心机器”的现象。托斯克注意到被诊断为精神分裂(当时还是个新词)的患者往往会认为他的心灵和身体正被只有他自己能看到的先进装置所掌控。他们在详细描述这些”摄心机器”时,常常以当时正在改变人们生活的摩登电器为蓝本。病人说,他们正在接受从暗处的电池、线圈和电气设备所发出的信号。他们脑中的声音由某些先进形态的电话或者留声机所传递,眼里的幻像则是由隐蔽工作的幻灯机或者电影放映机所投映。托斯克研究得最细致的是一位叫“娜塔莉亚·A”(Natalija A)的病人,她认定一伙住在柏林的医生正秘密地使用一台电气设备控制着她的思想,操纵着她的身体。那台设备的形状和她自己的身体相似,腹部位置有一个天鹅绒衬里的盖子,打开可以看到与她内脏相对应的电池。
活在真人秀里

维克托·托斯克(Victor Tausk)
尽管这些执念是荒诞不羁的,托斯克还是从中察觉了一些条理:这个快速演变的世界带来了幻想和噩梦。发电机为欧洲注入了活力,城市则被光亮所淹没。电力系统的分支网络跟教学幻灯片中人类神经系统的精细结构有几分神似。X光和无线电等新发现让当时尚未被窥知的世界展开在人们的眼前,神秘的力量在大众科学期刊上被反复讨论,在低俗的故事杂志上被言过其实,在通灵论者口中变成了“彼岸”存在的证据。但托斯克认为所有这些新奇之物并没有造成新型的心理疾病,而不过是这些现代发展为患者提供了用来描述自身状况的新颖词汇。
活在真人秀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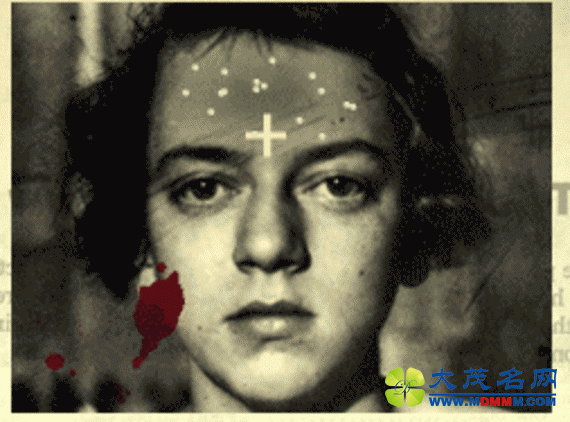
“娜塔莉亚·A”(Natalija A)
他认为,精神分裂的实质是“‘自我边界的缺失[3]“,它使得病人无法将自身意志加诸于现实,或者说无法形成有条理的自我意识。失去了自主意志,他们觉得仿佛有别人的想法和话语被灌输进了自己的头脑,然后从自己的嘴巴里讲了出来,而身体则是像木偶一样任人操纵、折磨、摆出古怪的动作。这些体验没有理性可依释,但那些受此之苦的病人还是抑制不住地感受到托斯克所谓”人类天生对’因果联系‘的渴望“。他们觉得自己受到外在邪恶力量的支配,他们的无意识用手头的东西编造了某种解释,这些解释常常会是令人眼前一亮的原创故事。病人无法为世界赋予意义,自己便成为了一个空瓶子,将围绕着他们的神话和假说统统装了进来。到了20世纪早期,许多人无法摆脱执念,认定暗中有操纵者利用先进科技折磨着他们。
沙漠牧民比较可能相信他将要被灯神用沙子活埋,而对都市美国人来说,则是被中情局植入了芯片而处于监控之中
托斯克理论的激进之处在于,他认为精神病人的言语并非胡乱拼凑,而是将集体信念和先入之见顺手拼凑得出的,而且它们常常构建得颇为巧妙。自古以来,人们基本上是在宗教框架内解释这类体验,它们被看做是邪灵附身、圣灵现身,巫术捉弄或是中了魔鬼的圈套。到了现代,旧观念依旧不缺市场,但我们得到了其他的途径来解释。托斯克观察到,精神病人看到的幻觉不是通常的三维物体,而是“墙壁和窗玻璃这些平面“上的投影。新出现的电影技术所带来的观感正与其高度相似,怎么看都是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一解释没有判断力上的缺陷,只不过它们根本不存在罢了”。
“摄心机器”体现了人们在直觉上认识到了科技的潜在力量与隐藏威胁,这一构思从未来主义的角度来看颇有说服力,甚至可以说具有惊人的先见之明。有记载的最早案例是在1810年,一个名叫詹姆斯·提利·马修斯(James Tilly Matthews)的病人绘制了精细的工程图纸,呈现的是正在控制他自己心灵的那台机器。这台他称之为“织布机”(air loom)的机器[4]利用了当时的前沿科技——人工合成气体和催眠光束将看不见的电流导入他脑中植入的磁铁,后者起到接收的作用。马修斯那个由带电波束(electrically charged beams) 和电流构成的世界对于他的同辈人来说是痴人说梦,现在却成了文化拼图(cultural furniture)的一部分,网上稍微一搜索就有发现十几个在线社区专门讨论“脑部植入电极”,无论是现实中的还是想象出来的。
活在真人秀里

一个名叫詹姆斯·提利·马修斯(James Tilly Matthews)的病人绘制了精细的工程图纸
古尔德兄弟以类似的逻辑对“楚门妄想症”作出了解释。看上去,“楚门妄想症”像是一种新的现象,一种对高度现代化的媒体文化所作出的新反应。但实际上,它只不过是装入了摩登新瓶的“旧酒”。妄想的内容和妄想的形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妄想在内容上可能是参差多样而且想象力惊人的,但它们的基本类型则具有"形式有限,而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特点。
拿被害妄想症举例,这种精神疾病在古今中外都有出现。在这类病例中,一位沙漠牧民会比较可能相信他要被灯神(djinn)用沙子活埋,而对都市美国人来说则是被中情局植入了芯片而处于监控之中。“精神疾病的一大特点是同现实脱节。”古尔德兄弟评论说,“但它们却又与时俱进”。与其说是病人与周围的文化相疏远,不如说是他们被文化所吞噬了:由于无法确立自我的边界,也因病人对社会威胁的超强感知,而往往只能听凭其摆布。
活在真人秀里

按照这种解释,“楚门妄想症“就成了——“自大妄想”(grandiose)这种常规类型的当代版本。病人在疾病发作时会认定世界正在经历微妙的转变,他们在世界这出大戏里被推到了舞台的中央。一切都突然被充满了意义,任何一个微小细节在他们眼里都举足轻重。你身边的人总是串通一气,扮演着预先指派的角色,考验着你或是在帮你为即将来临的真相大白的一刻做好准备。这类体验通常被解释为:圣灵造访、魔法变形,或者由于获得彻悟而进入了更高层次的现实之中。不难想象要是妄想症的症状毫无征兆地降临在自己头上,我们大概会立马得出结论说这肯定是哪档电视节目或者哪个社交媒体的诡计——由于某种被刻意隐藏的缘故,世界的目光突然聚焦在了自己身上,暗处的人们在兴致盎然地观看着我们遇事时的反应。所以,“楚门妄想症”不一定意味着真人秀节目是精神疾病的诱因或者症状;事实可能不过是,真人秀节目为我们这种难以解释的感觉和事件提供了一种说得过去的解释而已。
这些恰恰是过去好莱坞的高管们以为观众讨厌的东西:导演跟观众抖机灵,弄得观众摸不着头脑
尽管妄想的形成是无意识的,并且常常是对深重创伤的反应,但是为妄想作出合理解释的意图让它和小说创作有了许多共通之处。在极少数人身上,两者正好有了交集。1954年英国小说家伊夫林·沃尔(Evelyn Waugh)遭受了精神病的煎熬,这段时间他深受一种来路不明的声音的困扰,那个声音一直在数落着它的个性缺点,传播着关于他的恶毒谣言。他开始认定这些声音是最近那个BBC电台采访节目的制片人精心安排的,在录制节目时沃尔觉得那个人提出的问题有些无礼。无论沃尔走到哪里,声音都跟到哪里,沃尔解释说那些人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利用了与射电管“黑箱”类似的隐秘技术,后者正是他一个邻居热衷的爱好。他的妄想渐渐地变得华丽起来,就像沃尔后来描述他这段经历时说的那样:“这根本不像是失去理智……我一直在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结果我的思考能力在错误的前提之上拼命地运转,仅仅如此而已。”
沃尔将他的经历写成了一部精彩的喜剧小说——《吉尔伯特·平福尔德的折磨》(The Ordeal of Gilbert Pinfold)。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人过中年的作家,性格自大又脾气差劲。他越喝越多的利口酒和镇静药浇灌了他对现代生活的妄想症,直到后来病情恶化成严重的被害妄想(作者沃尔对被害妄想(persecution mania)很熟悉,他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小心用英文首字母缩写PM指代它)。尽管小说将作家自己经历的古怪联想进行了圆滑处理,对平福尔德的离奇窘境表示理解地眨了眨眼,但小说的剧情发展还是与作家精神错乱时的故事渐渐融合:就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能说清楚前者和后者的分界线。
活在真人秀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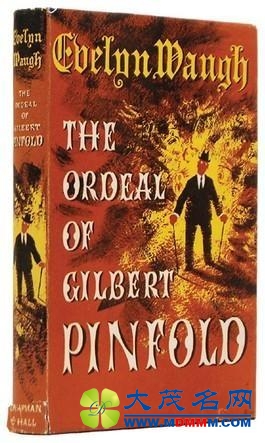
《吉尔伯特·平福尔德的折磨》
到《吉尔伯特·平福尔德的折磨》出版的时候,妄想症和精神病患者的故事正在从封闭的病房走出来进入流行文化的视野,心理疾病患者所作的第一人称回忆录摇身一变成了销量颇高的平装书。署名芭芭拉·奥布莱恩的作者写了《一个精神分裂患者的内心世界》(The memoir Operators and Things: The Inner Life of a Schizophrenic)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年轻姑娘被一帮神秘人追踪,坐着“灰狗巴士”横穿美国的非凡故事,那帮人是“操纵者”,手中拿着可以控制心灵的“频闪仪”。不过,这个故事是被包装成科幻惊悚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反过来,惊悚小说也正在将心灵控制的技术纳入其故事设定。理查德·康登(Richard Condon)的畅销小说《谍网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采用了这样的故事设定:受催眠的人仿佛编程机器人,会无意识地按照预设指示行动。小说的高潮令人难忘,事后想来其结局还诡异地作出了预言:一个受到催眠却不自知的特勤人员触发了预设刺杀了美国总统(译注:小说出版几年后,肯尼迪遭到刺杀)。康登这部不动声色的讽刺小说受到了冷战期间对洗脑的恐惧和对共产主义渗透的焦虑的影响,同时也对“阈下知觉广告”这个流行话题进行了吸收利用。(译注:Subliminal Advertising在消费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将产品图片、品牌名称呈现给观者的一种手段。)康登的小说巧妙地进入了心理学妖术诡计的争议领域:这是一个属于妄想时代的妄想寓言,在今天它仍然告诉我们,世上存在一个滋养着互联网阴谋论的隐秘世界。
活在真人秀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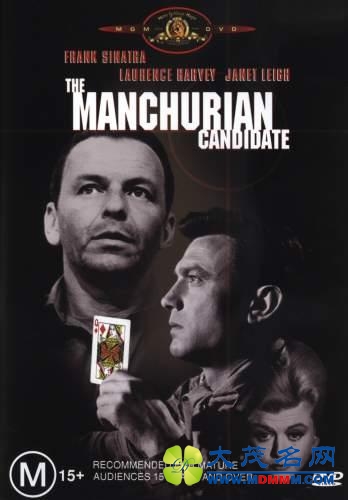
《谍网迷魂》
或许“摄心机器”在现代小说中的现身可以通过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的作家生涯和身后影响清晰地追溯。在他的身上,低俗小说作家的高产能力和他对自己患有精神障碍强烈臆想结合在了一起。他多次给自己下诊断认为自己得了妄想症和精神分裂,并把精神分裂角色写进自己的小说。他的小说和短篇故事更接近于精神病人的回忆录,而不同于同时代写机器人和飞船的科幻作家。书中喋喋不休地传递着一个观点:我们习以为常的现实实际上是由“摄心机器”刻画出来的,它是一个用来测试我们行为的虚拟世界,一套让我们维持日常生活的伪造的记忆,一些由渴望做大的企业兜售给我们消费者的幻象,一个由拥有读心能力的外星人编造的亲切故事……迪克的小说《脱节时代》(Time Out of Joint)与《谍网迷魂》同年出版,《楚门的世界》明显是从《脱节时代》中获得的启发。故事的主角雷吉·格姆(Ragle Gumm)渐渐地发现自己平淡的郊区生活其实是由军方的装置模拟出来的。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让格姆高高兴兴地玩着日报上他自以为是战舰谜题的题目,而实际上他的解题答案正指导着一场战争中的导弹袭击,而他对此浑然不知。
迪克当了一辈子“邪典“作家(cult author)。他数量有限的死忠因为他作品中特立独行的离奇元素而视之若珍宝,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象过这些元素能被吸收进入主流大众文化。事实上,在1974年迪克经历了一系列的幻觉发作,在此期间他阐述了一种复杂的个人宗教体系,此后迪克的作品变得更加兀自独立,甚至疏远了他那些喜欢科幻的忠实拥趸。他逝世于1982年,那年他的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被改编为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的电影《银翼杀手》(Bladerunner)。影片将故事情节处理得较为温和,制片方认为如果在故事高潮揭示主人公自己是个仿生人,观众会感到反感。之后由迪克的作品改编的电影,像保罗·范霍文(Paul Verhoeven)导演的《全面回忆》(Total Recall),也都柔化了原著中急转直下的剧情,在事情变得一清二楚之前,用一个开放性的结尾取而代之。
1999年,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创下了惊天票房,剧本中呈现了一个经典的迪克式的”摄心机器”,并且保留了迪克式的原汁原味。一个喜欢探听的黑客无意中发现了终极秘密:所谓的“真实世界”是模拟出来的,其背后的真相是:几个世纪以来,机器人一直将人类奴役并作为能源来利用。电影中出现了大段对话讨论剧情中的存在主义内涵,这些恰恰是过去好莱坞的高管们以为观众讨厌的东西:导演跟观众抖机灵,弄得观众摸不着头脑,拿“第四堵墙”[5]做文章。可这恰恰带来了成功,影片造成的轰动远远超出影院的范围,将它的文化基因注入到现已被互联网主导的广泛文化圈中。
活在真人秀里

正如美国剧作家威廉·戈德曼(William Goldman)在他名为《银幕春秋》(Adventures in the Screen Trade)的回忆录中写道的那样,在电影界,没有人知道所有的一切。或许一部同样大胆的超小说(译注:metafiction现代小说流派,忽略传统写作中对真实性的关注)在多年以前也能够收获成功,但更恰当的解释是《黑客帝国》造成的文化冲击反映了交互式数字媒介在新千年到来之际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程度。在彼时彼刻网络社会的数量达到了可以掀起波澜的临界点: 十年前,那些未来主义色彩的观点还是为那些阅读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或者网络文化杂志《Mondo 2000》的先锋派所独有的,到了今天这个全球化数字时代,却成了人们日常生活脉络的一部分。将菲利普·K·迪克的影响力仅限于邪典小众的那令人晕眩的逻辑,如今已为作者赢得了广大受众。那些消解了现实和虚拟之间那条界限的费解讽喻突然就让大家来了兴趣。
詹姆斯·提利·马修斯在疯人院病房里画出“织布机”发出的那些看不见的波束和射线的时候,他是在描绘一个仅仅存在于他脑海中的世界。而现在我们的世界成了他所描述的那个样子:我们数不清每时每刻有多少波束、射线和信号正在穿过我们的身体。维克托·托斯克认为”摄心机器”的念头之所以会出现,原因是病人无法将外部世界和自己的心迹分辨清楚,当病人创造出一个外因来解释他自己的念头、梦境和幻觉时,这一困惑便得到了解决。而电视、电脑、虚拟、交互这些现代词汇则模糊了感官和现实之间那传统意义上的差别。
当我们在露天大屏幕上观看赛事直播,或者在自己的卧室里关注突发新闻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在接收闪动的图像,而我们的心却和远处的千万人一起律动。我们在Skype的时候面对着朋友的二维影像,在社交媒体的个人档案中塑造着完美的理想自我。有了虚拟化身和马甲,我们可以快速地开始一次匿名而又亲密的交谈。网络游戏和在线社区所构建出的虚拟现实不但可以量身定制、满足各个玩家的需求,而且和《楚门的世界》故事里一样无所不包。泄密和曝光不断地刷新着我们对自己在向谁透露着什么,我们的行为有多少观众,想法能传到多远的地方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我们的身份被自己篡改着,也在被不知名的其他人所篡改,我们无法清楚地分辨真与假、什么是隐私什么不是。
到了21世纪,”摄心机器”走出了精神病院里那带百叶窗的病房,成为了这个时代一个独特的神话。它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是因为我们都得了精神病,而是因为现实已经成为了外部世界和我们内心想象这黑白两极之间的灰色地带。这个世界一方面被成就它的技术所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内心的认知机制不断地将数字世界的幻象剪辑进自我意识这部私人影片当中。关于蜕变的经典神话探讨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边界、我们与生灵、与神灵的关系。同样地,那些空想的科技曾一度被认为是精神错乱的标志,现在却让我们弄清楚了那些正将我们的精神世界拓展至陌生维度的技术能创造何种可能,带来何种威胁,具有何种局限。这听上去极具诱惑,却也让人不寒而栗。
活在真人秀里

|  |客服:0668-2886677QQ:75281068|大茂微博|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大茂名网
( 粤ICP备18149867号 )茂名市大茂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客服:0668-2886677QQ:75281068|大茂微博|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大茂名网
( 粤ICP备18149867号 )茂名市大茂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