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马上注册登陆,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用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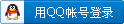
x
“弼马温”不止孙悟空当过:中国古代的动物职官

有证据表明,早在商代后期,商王已委任专门官员负责动物的采办、饲养、训练、保健。甲骨文记载,料理猎狗和饲养马匹都有专门官员负责。商代铜器铭文也有大量跟畜牧相关的文字,有表示兽栏、棚厩、鱼塘的字,还有表示养兔、养牛、养鹿所用围栏的字。此外,甲骨文还保留着与狩猎活动有关的大量词汇。这些记录,再加上动物遗骸,都证明商人在面对自然环境时具有高度的组织水平。牧牛、驯马、养狗的职官也见于周代青铜器铭文。
从战国两汉文献可见,照管动物的职官为数众多,其中有些职官在周代早期可能已存在。《周礼》是古代中国文献中动物资料最丰富的一种。在它所表述的宇宙论模式中,跟自然界打交道的人类活动,事无巨细都安排在“官”的秩序里。《周礼》所呈现的世界观,是把现实世界和人类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来分别部居,结果实质上就是个官僚秩序。《周礼》原名《周官》,是对周王朝行政结构的描述,详细记录了各类政府官员及其职责,其中“动物职官”的数量是很可观的。他们按部就班,分布在现存《周礼》的每个一级标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下,可见每个主要的政府部门,都有管理自然界这项职责,这为深入了解战国时期的动物观念提供了许多珍贵信息。诚然,现存文献未必反映周代官僚机构的实际情况,而只是表现了汉代人对周代朝廷职责的相当理想化的认识。不过,考虑到其中大量的“动物职官”也出现(有的以不同的头衔出现)在其他尚欠系统的战国文献中,很可能这些职官有不少是早就以某种方式存在的,然后才编入《周官》。《周礼》还将一些比较普通的行家里手纳入编制,其中也有跟动物打交道的专门人员,如相士、兽医、驯兽师。
《周礼》对职官的描述有个标准格式,即先列其名,次述其责。如以下条目就叙述了饲养动物以备祭祀的“充人”的职责:
充人,掌系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则系于牢,刍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系于国门,使养之。展牲,则告牷;硕牲,则赞。
动物从出生到祭坛,每个阶段都有人管理,这就构成了官员的链条,“充人”就是这链条中的一环。链条里的环节还有牧人,有棚厩和苑囿里的管理人员,以及保管祭肉的人等等。再如“牛人”,负责饲养国家公务所用的牛,他所养的牛除了充当祭礼和丧礼的牺牲,还用来招待国宾,供应军需等。还有官员负责装饰供祭的牛,他要把横木拴在牛角上以防伤人,穿牛鼻以便牵引,还要备好水和柴以便行仪时清洗、烹煮。见于《周礼》的职官不止这些,他们的职责也很广泛,比如搜求异域动物,汇集祭肉,饲养、放牧并训练家畜,驯化野兽,给动物治病疗伤,管理动物贡品和猎苑,照料动物棚厩,为礼仪准备动物,征收兽角和鸟羽作为赋税,解决动物相关的法律争端,驱除有毒动物,安排渔猎时令,驱逐鬼怪禽兽等。动物世界的每个方面都有相应的职官。《周礼》把理想国家描述为整个宇宙的摹本,当然也就认为自然界受官僚体系的控制。
这个官僚体系横跨人与自然两个世界,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人们对动物的关注在根本上同社会政治和礼仪分不开。《周礼》中的官吏并不负责观察形形色色的生物,也不必搜集经验资料并加以解释,他们的职责是把动物及其相关现象整合到人间政治组织的权力范围内。此外,由于料理动物是在官僚模式里进行,动物界就成了礼制秩序的组成部分。陆威仪(Mark Lewis)指出,《周礼》在描述职官时,并没有把每个职官的日常事务跟宗教性职责分开,相反,行政职责和宗教礼仪的职责是并行的。在《周礼》所描述的理想国家里,官员身兼二任——既负有实际管理之责,又在宗教仪式中承担角色。自然界呢,由于许多官员奉命管理它,许多职责针对它设置,于是它也身兼二任——既是自然的世界,又是个礼仪性、宗教性的领域。说到与动物打交道的职官,《周礼》总是把他们的两种职责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是世俗事务,如放牧和饲养;另一方面是为了国家礼仪或宗教祭祀的需要而照管动物。上文提到为国家养牛的“牛人”,就是这样:他既要为军队供应牛肉,为祖先亡灵提供牺牲,又要备好盛放牛血的容器和悬挂祭肉的支架等祭器。“?人”则不仅掌管王室辖地的渔业活动,还为祭礼供应鲜鱼和鱼干。跟动物打交道的国家官员,既负责实际事务,又掌管象征性活动,无论是烹煮鸟兽、供应饲料这种粗活,还是凭借预言捣毁不祥鸟的鸟巢,都归他们管。
管理动物界的每项工作都指派了专员负责,这么一来,对动物的操作和料理就只是因为对人事有影响才受人重视。结果,形形色色的动物就分别归到一些社会性类别和礼仪性类别里去,虽然这些类别本来是人类用来塑造社会的。人给自然界施加了这么一个模子,也就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对动物物种的形式化描述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是由动物的社会性功用决定的,而不取决于动物的生物学属性。《周礼》中的自然界不是博物学家研究的对象,而是行政控制的对象。人们记录动物,给动物分门别类,是因为社会生活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比如为了准备食物、采办牺牲,或者把动物当作纳税的商品和公私财富的标志,就都要对动物进行登记和分类。
社会性和礼仪性动机影响了动物分类,这点可以从《周礼》对不同类型的马的详细说明中看出来。从讨论相马术和兽医的专门文献可以知道,战国秦汉时期,马是贵重的商品,主要原因是马在运输和战争中很有用。司马迁叙述汉帝国的经济状况,就屡次以马匹多寡为依据。例如,天子不能备齐毛色相同的马匹来供车舆之用,将相不得不乘牛车,都成了财富匮乏的明证。而马匹富裕则说明了相反的情况。所以司马迁写道,汉帝国稳定以后,“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
从《周礼》可见,大家之所以要给马分门别类,就因为马是具有社会性的财产。据载主管王室马厩的“校人”把马分成六类(“辨六马之属”)。文中先交代名称,后面跟着限定语“一物”的,就表示这是一类。这六类是:适于繁殖的“种马”、适于军用的“戎马”、适于在典礼上展示的“齐马”、适于旅行的“道马”、适于畋猎的“田马”、适于劳作的“驽马”。这样,“校人”就根据功用把马分为恰当的类别。区分的标准不是生物学上的差异性,而是决定动物在人类政治组织中可以派上什么用场的形貌特征。另一官员“马质”,掌管马的采购和估价。他根据价格另行分类,把马分为戎马、田马、驽马三类。其他官员只要涉及动物或牺牲的辨别、分类,也运用相同的模式。多数情况下,辨别动物是由于礼仪、社会和宗教的需要。
《周礼》把职官与特定的动物物种联系起来,因此有个一般倾向,即,不去解释某种动物怎样活动,而是说明人怎样对付动物。所以《周礼》记载了数量可观的从事驱邪、祈神的动物职官,他们的活动是为了使人远离有害动物,或从人的利益出发去控制某种动物。庶氏用咒语驱除毒虫,翨氏负责攻击猛鸟,射鸟氏射杀祭祀时出现的凶鸟,硩蔟氏捣毁不祥鸟的鸟巢,翦氏烧草熏走毒虫,蝈氏驱赶蛙和黾,壶涿氏驱水虫,庭氏射杀国中的不祥鸟,都是如此。
总之,《周礼》的作者无意根据动物的自然属性把动物界整理为原始科学的系统,他(们)的目的是把动物界整合为社会性的动物志,把动物的种种自然行为分门别类,安排到官员的职责范围里。《周礼》对动物界的叙述并不是聚焦在动物或动物行为本身,它只考虑对人发生影响的动物行为。文本中有些部分乍看起来像是动物学资料,研究科学史的一些中国学者倾向于把这些部分筛选出来,以证明古代中国已经存在或即将产生对动物的科学研究。照我看,这种倾向不能说是合理的。比如《周礼》有个段落讨论相角的问题,相当详细地分析了牛角的长度、颜色、质地、弹性,很像是生物学的描述。但是从上下文却看不出任何动物学或生物学的旨趣。该段落出自《考工记》,而《考工记》是用来替代《冬官》篇的,目的是指导弓匠妥当使用牛角或鹿角来造弓、饰弓。这个段落固然表达了生物学知识,但上下文的根本关切却是人的工艺。“梓人”一条也常见征引,用来证明古代中国存在科学的动物分类学。该条目把动物分为“大兽”和“小虫”两大类,各有若干分支,固然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生物学知识,对这段话的上下文却不该视而不见。文中叙述的是乐器装饰的问题,作者指出装饰乐器的动物有什么自然属性,主要是为了把这些属性与乐器的声音联系起来。还有一个段落认为动物的外貌、行为跟味道有关系,于是把动物相术和对动物行为的观察都纳入烹饪和祭祀的框架:
牛夜鸣则庮。羊泠毛而毳,膻。犬赤股而躁,臊。鸟皫色而沙鸣,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马黑脊而般臂,蝼。
和上面提到的例子一样,观察动物、搜集资料在这里也是为人的需要服务,目的是为祭祀仪式和王室宴飨选用美味。
人间政治组织把动物纳入麾下,这种情况从《周礼》看得最明白,战国两汉的其他文献也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一点。《左传》里有两个故事,说到官名与自然界的联系,还说到任命官员管理动物,由此可见这两种观念可能早在《周礼》对理想制度的描述之前已经存在。第一个故事说,郯子(约活动于公元前524年)访问鲁国时,解释了他的祖先少皞为什么以鸟名官。他说古代传说中的五帝各订历法,又说五帝的统治分别有云、火、水、龙、凤等祥瑞昭告于世,因此他们用这些祥瑞来制定官名。鸟名作为标志,是因为少皞即位时有凤鸟出现。接着,郯子列出了少皞治下以鸟为名的官职:掌管历法的,称为凤鸟氏;掌管春分和秋分的,称为玄鸟氏;掌管夏至和冬至的,称为伯赵氏;掌管立春和立夏的,称为青鸟氏;掌管立秋和立冬的,称为丹鸟氏;司徒是祝鸠氏;司马是雎鸠氏;司空是鸤鸠氏;司寇是爽鸠氏;司事是鹘鸠氏。文中接着说,“五鸠”之官聚集民众,“五雉”之官管理五种工匠,“九扈”之官管理农业的九个方面。这段话所注意的是动物名与职官的联系。少皞治下的官名由鸟名构成,这件事本身倒是次要的,因为他的前任也都是根据自然界的预兆来命名职官的。关键在于故事透露了一种观念:传说中的圣人是借助自然现象来安排历法和官名的,而历法和官名本是他们赖以统治的基础。郯子的解释之后,紧接着有一段议论,提到孔子曾向郯子学习“官学”。可见这个故事要强调的是明了官名来源的重要性。同样的观念还见于后来的《抱朴子》,书中也提到了《左传》里关于孔子的这个段落,说他“问郯子以鸟官,官有所不识也”——不是说孔子不懂得鸟,而是说他不能把鸟名与官制联系起来。孔子不能在某“物”与某“官”之间建立联系,而他想要了解的是鸟名为什么用来为职官命名,又怎样为职官命名。这里的逻辑是,鸟的行为与官的职责有对应关系。这正是上述《左传》段落的主旨。比如说,爽鸠是凶猛的鹰隼,责在擒拿盗贼。伯赵夏至始鸣,冬至乃止。凤鸟知天时,所以历正之官名为“凤鸟氏”。这种叙述的背后有个预设,是认为人间的职官与自然界的现象相对应,自然界的预兆是官名的来源,所以,熟练掌握自然界是熟练掌握官制的表现。故事的最后说,少皞的后继者在安排历法时再也不能凭借远来的天瑞,而只能依据人事了。
《左传》的第二个故事说的是养龙。据称公元前513年,龙见于晋国国都,于是晋国太史蔡墨详细叙述了古人怎样养龙,国家又怎样使“豢龙氏”和“御龙氏”两支家族为此效劳。故事按时间顺序概述了这两个职官的兴替,说在舜的治下和此后数代,养龙是成功的。因为一直有龙出现,舜时候负责养龙的官便获赐“豢龙”为氏。到了夏的第十三个统治者孔甲,豢龙氏后继无人。那时天帝赐孔甲两对龙,孔甲不能饲养它们,又不能找到豢龙氏家族的人。于是,另一个家族的后裔由于曾向豢龙氏学艺,便奉命饲养孔甲的龙,赐氏为“御龙”。这名官员却玩忽职守,把一条神龙的肉作为美味进奉君王,因此再也不能担任该职,也不配称为“御龙”。到此为止,故事是清楚的,意思是孔甲是第一个不能照料神龙的君王。不能养龙,是他不能统治天下的标志。结果,龙也不再现身于君王无德之世。不过接下来的叙述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转折。有人问,为什么当今没有龙出现,蔡墨答道:
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郁湮不育。
蔡墨接着说古人因此立“五行之官”,并列出了这些职官及其主管的神灵。他指出龙是“水物”,又说由于“水官”已经废弃,龙就再也不能给人活捉。照这个说法,孔甲之所以要为龙的隐没负责,就因为他失于任贤,没能任用养龙的行家。孔甲的过失在于没能把恰当的“官”与恰当的“物”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他不能把料理龙的任务成功地纳入朝政。
这节文字在五行思想的发展史上很重要,因此备受注意。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认为,故事所说的五行各有神灵掌管,是对国家的类比。乐维(Jean Lévi)说这里的官僚体制“象征性地再现了宇宙”。陆威仪认为少皞鸟官的故事“是个寓言,表示宗教权威转变为凭借仪式和宇宙论进行统治的行政政府”,又说政治化的神灵世界本来以世系为基础,后来转变为以职官为基础,而孔甲的故事就是这个转变的早期例证。从豢龙氏的故事的确可以看出官职世袭制的出现,这个故事还把维持和传承官职的制度投射到了神灵世界。但我认为故事所表现的人神两界官制相应,受到了过分的强调。照我看,这节文字并不意味着人把自然界简单地看作国家官僚体制的镜子,而是表现了人凭借官僚机构把自然现象和鸟兽精灵都控制起来。从孔甲的故事可见,成功的统治一定有称职的官吏在料理龙。以此为基础,有一种看法认为卓有成效的官僚体系一旦崩溃,野兽就要接管它的职责;还有一种看法,以为祥瑞动物的出现跟政府的贤明高效分不开。这两个主题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讨论。
上文说到不少动物职官的官名,这些官名所用的字眼也值得注意。从《左传》的这两个小节来看,官名都有“氏”字。许多中国学者仍然认为这些故事是远古时代存在动物图腾崇拜的典型例证,他们认为从这个后缀来看,职官与古老的动物图腾分不开。其实把上述动物职官的起源跟原始动物崇拜联系起来并没有确凿证据,也没有其他形式的仪式行为可以证明某些动物物种与某些社会群体确有关系。动物、天象和其他自然现象,在古代中国当然也作为标志来使用,比如《尚书》记载,舜曾要求一见天子祭服上所绘的“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杂色雉)”,但要说以动物名官起源于原始图腾却靠不住。
与其说《左传》故事中的“氏”起源于图腾崇拜或者跟神话中的龙族有关,不如说“氏”指的是家族或宗族。陈奕麟(Allen J. Chun)说,“‘氏’很显然关系到诸侯国的政治级别和供奉之礼……赐‘氏’多半是对个人懿德美行的嘉奖,表示政治上的恩宠和连带的礼制义务,只有这样理解‘氏’才是合理的”。那时有的行家凭技能从事某个行业的管理,也可以称“氏”。“氏”本来有一层含义,表示因受封而有忠君的义务。这种贵族化的内涵此时未必还保留着,考虑到这点,以上的解释就很接近“家族”或“行会”的意思了。某个行业的职责在同一宗族代代相传,精通同一种技艺的几个群体又形成若干家族,这就是《左传》里的“豢龙氏”和“御龙氏”。职业世袭与公认的国家官职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形在《左传》里还有一处记载——一位鲁国大夫讲得很明白:“官有世功则有官族。”意思是官职如果代代相传,官名就可能成为族姓。再看《周礼》对理想化国家中职官的描述,头衔中缀有“氏”字的官吏不少于55种,其中有些是负责料理动物的(如“服不氏”,“射鸟氏”、“罗氏”、“冥氏”、“穴氏”等)。可见《周礼》中的“氏”字指统治者认可并雇用的行家(或行家的家族),那么,见于《周礼》的不少动物职官很可能来自行家里手的家族或宗族,他们是把料理动物的本领薪火相传的人。
对自然界及其生物的保护和控制跟官僚系统有一种辩证关系,这点还可以从汉代早期的一则轶事看出来。故事说的是动物登记册的保管。据载文帝(前180—前157年在位)曾向上林尉问禽兽簿,反复问了十几遍,尉和左右都答不上来,这时掌管虎圈的下级官吏上前代尉作答。他的回答十分详备,喋喋不休,于是文帝认定上林尉不胜任,并下令提拔这位下级官吏任上林令。但文帝接着就受到一位进谏者的盘问和责备,批评他倚重“口辩”胜于“实”;这就是说,皇帝应该倚赖书面记录和恰当的官吏。故事说的也是靠官僚系统来治理的问题。故事里的统治者受到告诫,要他尊重官吏的等级。其次,轶事强调了任命恰当官吏来管理禁苑动物的重要性。最后,从这条材料可见畜产有官方记录并有人保管,也可见书面记录比口头说明更受重视。皇帝要了解自己的畜产,得通过保管记录的官员。只有这位正式任命的官员才可以向皇帝简要介绍畜产,即使下属比他熟悉也不能越俎代庖。所以,官员要各司其职,否则就不能可靠地管理上林苑动物,而统治者的权威也会因此受到损害。
事关动物,就由相应的官员去料理,换句话说,“正官”反映了“正名”。《淮南子》有一则故事也表现了这种观念。故事说孔子在野外把马给丢了:
孔子行游,马失,食农夫之稼。野人怒,取马而系之。子贡往说之,卑辞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太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过也。”乃使马圉往说之。至,见野人曰:“子耕于东海,至于西海。吾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马而与之。
这故事里贯穿着几个主题。首先,讨回走失的马似乎是件小事,孔子是不会直接去交涉的,所以先是派了弟子去,接着又派了地位更低的使者去。故事暗示,马的下落或者说动物的情况,在圣人而言算不上要紧事。据《论语》记载,有一次马厩失火,孔子问人不问马,和这里的道理一样。上面的故事说明圣人与动物界的联系是间接的,第五章将说明,圣人对牺牲和蛮夷(据说他们和动物相近)的态度也有这个特点。其次,圣人处理起动物的事情来,是通过任命合适的官吏,这就形象地表现了“正官”的主题。马的事情要留给管马厩的人去办,只有这小吏才掌握跟农夫和解的本领、语言和天生的老练,因为在孔子眼里,马倌也好,农夫也好,都接近动物的水平。这一故事有个较早的版本见于《吕氏春秋》,就不称“马圉”,而称之为“鄙人”。为了达到目的,孔子不去直接追讨走失的马,他最在意的似乎是派什么人去交涉才是正确的安排。他的态度使人想起,圣人对于直接分析自然界是明智地加以回避的。就像圣人不去研究生物学的动物,而是通过命名立号来整顿动物界的秩序一样,他也不去直接管理动物,而是通过命官设职来料理动物。
“弼马温”不止孙悟空当过:中国古代的动物职官

|
|
 |客服:0668-2886677QQ:75281068|大茂微博|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大茂名网
( 粤ICP备18149867号 )茂名市大茂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客服:0668-2886677QQ:75281068|大茂微博|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大茂名网
( 粤ICP备18149867号 )茂名市大茂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