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马上注册登陆,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用户注册

x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新晋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个繁忙无比的人。和其他专注在书桌前潜心创作的作家们不同,这位白俄罗斯的女记者,习惯带着她的录音设备和笔记本满世界飞奔,“带着真诚和快乐,继续做着自己渺小的工作”。
2016年初,她的“乌托邦之声”最后一部——《二手时间》的中文版面世,我们第一时间给她发去了详细的采访请求。两个月后,在漫长而焦灼的等待中,67岁的阿姐发来近一万四千字的回复。
据说,为了回答中国读者这些问题,她写了好几天。我们截取其中的七分之一,让每一个着迷于俄罗斯民族复杂性的读者,让每一个对自由的含义有理解困惑的读者,一睹为快。如果您有兴趣畅读书评君与阿列克谢耶维奇访谈的完整版,敬请关注近期出版的新京报书评周刊。
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1948年生于乌克兰(原属苏联斯坦尼斯拉夫地区),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代表作品有《战争中没有女性》、《锌皮娃娃兵》、《死亡的召唤》、《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等。2015年10月,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
“怪物活在我们的生活中,它却被称作自由”
采写|新京报记者柏琳
特约俄文翻译|张猛(特此致谢)
生为一个小人物,你究竟愿意存活在伟大的历史中?还是满足于平庸的生活中?对于苏联解体前后二十年里,生活在那片广袤土地上的俄罗斯人而言,这是一个永恒的难题。
你可能不知道,2016年,是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乌托邦》发表500周年。世世代代,无数人类试图在地球上建立天堂的梦想,从未熄灭,阿列克谢耶维奇看到了这一点,她无不悲哀地预测,“红色乌托邦还将会长久地对人进行诱惑”。
“红色乌托邦还将会长久地对人进行诱惑”
新京报:在谈这本书之前,我记得你曾说,无论是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还是塔吉克人……说到底都是同一种人,叫做苏联人,那么你觉得“苏联人”区别于其他人群的特性是什么?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俄罗斯,或者说苏联,最大的特性在于,我们的资本是痛苦。这是我们经常获取的唯一的东西。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气,而是痛苦。我怀疑,在我的书中,正是它吸引了西方的读者,让他们觉得惊奇。就是这种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活下去的勇气。今天到处都需要这种勇气。在萨拉热窝就曾是这样。不可计数的坟墓。人不仅被埋在坟地里,还被埋在运动场上,公园里。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就像恐怖故事… 他们将水泥填进小女孩们的阴部,甚至还有(更恐怖的)… 一句话,一个人体内的人性所剩无几。只有薄薄的一层。为了活下来,俄罗斯的经验是需要的。
俄罗斯的文化中,具有人类在地球上建设天堂的最天真、最可怕的尝试,最终这一尝试,以一个巨大的兄弟般的坟墓告终。我认为,做完这项工作是重要的,因为红色乌托邦还将会长久地对人进行诱惑。
阿列克谢耶维奇:红色乌托邦将长久地对人进行诱惑

《二手时间》
新京报:《二手时间》是你的“乌托邦之声”的最后一部,你会如何描述这本书?
阿列克谢耶维奇:它讲的是最近几年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我们期待了那么久,但所有人都很失望,无论是曾经持不同政见的人,还是商人、共产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甚至是流浪汉。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大街上的人比作家们更加有趣。
这本书的先声和草稿,是《被死神迷惑的人》,一本描述社会主义帝国废墟上自杀事件的书。一幅解体后的心理肖像画。
我选择了那些与时代紧紧相连,像粘在胶水上的飞蛾一样,粘连在时代上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与一种思想之间画了等号。今天这显得怪异、不正常,而当时那就是我们的生活。这都是一些诚实的、坚强的人——阿赫梅罗耶夫元帅、女诗人尤利娅·德鲁仁娜、1941年布列斯特要塞英勇的守卫者季梅林·基纳托夫……
新京报:《二手时间》里的见证,是更为琐碎、隐藏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的一种“看不见的见证“。你认为《二手时间》和前四部作品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是我所有的书中最复杂的一本。很难在一些碎片上描写一个庞大帝国的解体。这些碎片形态各异,它们竭力远离强制俄罗斯化,远离帝国性,希望过自己的民族生活。在交谈中显现出众多的思潮、观点,要把所有这些组合成一个题目非常复杂。庞大帝国解体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急转弯完全震惊了世人。这种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逆转在历史上还从没出现过。
新京报:有媒体评论称《二手时间》讲述的是对苏联的怀旧之情,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不同意那种说法。我写的是“红色人类”的百科全书,一种乌托邦的历史。我使所有人发出声音。不知为何流传着这样一种看法:好像一写苏联人,就一定是在体验一种怀旧情绪。其实并不是这样。为了理解我们曾生活过的时代,我使所有人发出声音。每个人都在说出自己的真理。我本人是一个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但为了勾勒出那个时代的形象,我应当听各种各样人的声音。
阿列克谢耶维奇:红色乌托邦将长久地对人进行诱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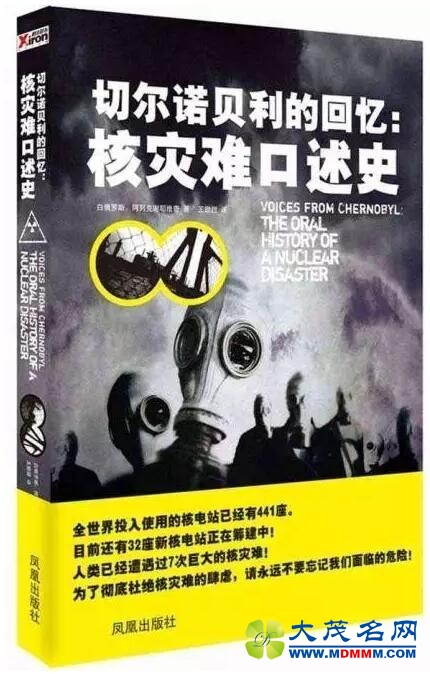
《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
“人变得更加开放,却不自由”
新京报:从“乌托邦之声”的第一本书《战争中没有女性》到最近的这本《二手时间》,你是否认为书里的主人公发生了什么变化?
阿列克谢耶维奇:现在唯心主义的人变少了。甚至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也感觉自己被骗了,他们从那个大馅饼中什么也没有分到。除了那些躺在盒子里的奖章,他们没什么给自己的子孙。而对于他们的孙子来说,这些奖章已经一文不值。现在人们谈论自己的时候更加坦率,他们原原本本地谈论一切。
也就是说,如果阅读我们的经典文学和苏联文学作品,以前仿佛不存在生物学上的人:那些作品中没有一个具备内脏器官的人。为什么人们会读西方文学?因为那里谈到了身体,谈到身体的秘密,谈到爱情既是美好的,又是可信的。而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文学中一点也没有!而如今人们聊天已经百无禁忌。人变得更加开放,却不自由。
我没有见过自由的人。所有人多多少少还像苏联时期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被束缚,被定在某种经验之上。但坦诚已经显露了出来,致力于某种宽阔的才能已经出现,词汇量在发生改变。我在我的新书中要写的恰好是这种感官的新脉络,词汇的新脉络。
阿列克谢耶维奇:红色乌托邦将长久地对人进行诱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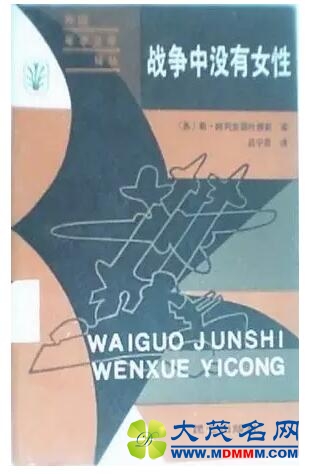
《战争中没有女性》在中国译介的最早版本
新京报:苏联解体后,上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发生的种种,你会给出怎样的评价?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评价90年代时,我会更加小心。不管怎么说,这曾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还记得,人们的脸转换得多么迅速,连行为举止也是。自由的空气令人迷醉。我的年长朋友那一代人直到现在还坚信:“我们生活幸福。我们想推翻苏联共产党,后来我们就把它推翻了。” 但剩下的问题是:我们要在这块地方建什么?那时我们想:数千人读完了《古拉格群岛》,一切都要改变了。
今天我们不仅读了索尔仁尼琴,还读了拉兹贡,还读了丽姬娅·金兹博格……然而改变得多吗?不久前我在画家伊利亚·卡巴科夫那儿找到了表达现状最准确的形象:以前所有人和一个巨大的怪物作斗争,这种斗争使得一个小人儿变大了。等我们战胜了这个怪物,四处回望,突然看到,现在我们需要和老鼠们生活在一起。在一个更加可怕,更加陌生的世界。各种各样的怪物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人的种属里钻来钻去。不知为什么,它却被称作自由。
阿列克谢耶维奇:红色乌托邦将长久地对人进行诱惑

2015年10月8日, 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新京报:在《二手时间》的开篇你曾提到,在为创作这本书而进行走访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无论你遇见苏联时代还是后苏联时代的人,总会问同一个问题:自由到底是什么?而两代人的答案是截然不同的。你是否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自由的不同理解,是构成苏联和后苏联时代两代人迥异精神面貌的根本原因?
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我们为自由所承受的痛苦,其意义何在?如果不管怎样都会重复,它们又能教会啊我们什么?我经常问自己这件事。当我向我的主人公们提出这个问题时,它迫使人陷入措手不及的状态。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痛苦是一种自我价值的体现,是他们最主要的劳动。但事实证明,痛苦并不能转化成自由。阿赫马杜林娜写过这样的诗句,“刽子手和受害者在同等程度上毁坏了孩子纯真的梦”。而沙拉莫夫的话更加残酷无情——“集中营的经验只有在集中营里才被需要”。我没有答案。我应当诚实地承认这一点。但我从小就被恶与死的主题折磨,因为我成长在一个战后的白俄罗斯农村,在那里每个人谈的就是这些。
新京报:获得诺奖之后,在接下来的创作中你是否会暂时放下苦难,去关注一些轻松的主题?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将继续从事自己渺小的工作。带着真诚去做,并且,您知道吗,带着快乐。尽管写作困难重重,但这个世界总归还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人,在美国,德国,波兰……以及国内。
当宣告我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时,白俄罗斯人走上明斯克街头,互相拥抱、亲吻。而独裁者卢卡申科没有什么好话送给我,他说,我“给国家抹黑”。当斯大林谈到布宁和帕斯杰尔纳克,勃列日涅夫说到布罗茨基——这些俄罗斯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说的也是同样的话。过去了50年,独裁者还一点没变,甚至是用词。对于艺术家来说,街垒不是最好的地方,但是我们还不能从那里离开。时间不放我们离开。
阿列克谢耶维奇:红色乌托邦将长久地对人进行诱惑

|
|
 |客服:0668-2886677QQ:75281068|大茂微博|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大茂名网
( 粤ICP备18149867号 )茂名市大茂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客服:0668-2886677QQ:75281068|大茂微博|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大茂名网
( 粤ICP备18149867号 )茂名市大茂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